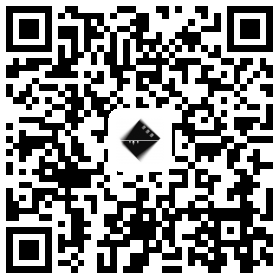莱比锡国际纪录片动画电影节(DOK Leipzig)始于1955年,1995年增设动画单元,每年秋天在德国莱比锡举行,历史悠久。同时也是全球五大纪录片电影节之一。

图片来自:DOK Leipzig官方网站
https://www.dok-leipzig.de
2021年10月25日—10月31日第6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与动画电影节(DOK Leipzig)如期举行,邓伟导演凭借纪录电影长片处女作《父亲》在众多佳作中脱颖而出,一举囊括国际主竞赛、国际影评人奖、跨宗教评审团奖三项提名奖,并斩获国际长片主竞赛单元「金鸽奖」。

60年来华语纪录片首次获得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与动画电影节国际长片主竞赛的金鸽奖,这也是该电影的最高荣誉。同时《父亲》也入围2021年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提名”评优单元。

《父亲》剧照

《父亲》剧照
若家人遭遇重大变故,拍摄者将自己置于画面何处?本片中,导演的摄影机如手术刀般对准了父亲与爷爷,冷静或是冷酷?不管是导演还是观众,都并不容易判断。
——IDF2021复审评委推荐词

《父亲》海报
纪录片简介
血脉作横樑,以此撑成家。只是一个屋檐下,有时偏是血亲才结梁子。祖父目成盲,帮别人算了一辈子的命,能看命宫,却守不住自己房舍。爸爸成了建设公司老板,盖别人的家,回头却要拆自己的房子。现代化浪潮下都市化进程摧枯拉朽,时代如推土机开来,家如何成家?屋檐下闹革命,爸爸处处求生,爷爷动辄说死,老屋子里暗稀微,多少故事如尘埃在光影里飞扬,且任镜头游移,空间里丈量时间,几代故事,各自悲喜,体察情感格局,看两代亲情动线怎么腾挪闪移,各有各的理,毫不相让,有时软砖头,打在身,痛在心,有时铁门槛,跨不过就是跨不过。大破坏与大建设,相近又远离,是一页家史,其实是家族史,更是时代转型之交属于一个人的生命史。陋屋豪邸,阳宅阴宅,生求一块地,死葬一块地,聚散有时,兴旺有时,生有时死有时,房子有时,但家是永远。
《父亲》于2021年10月22日和24日分别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放映两场,同时也为各位纪录片爱好者带来了精彩绝伦的映后环节。
展播时间:10月22日14:00
蝴蝶剧场
嘉宾:邓伟(导演)
主持:沈健文

A:这部片子是我研三时候作为毕业作品去创作的。家庭这个题材一直是我放不下的东西,但我从摄影画面先行的角度去看,我家的环境怎么拍都不入画。后面机缘巧合回了一趟家。深秋下着蒙蒙细雨,父亲在工地前处理焦头烂额的样子。那一刻的画面,我完全被打动了。我拿着很差像素的手机,拍了一张照片,觉得这个片子肯定能成。我就直接退掉了其他项目,让朋友把北京的相机寄回来,开始拍这个片子。
Q:面对过于私人的情感和故事,是如何克服自己去克制的表达情感的?
A:凭着感觉去做。拍摄身边最亲近的人,会很难。侄子摔倒时,我会下意识去扶,但想起自己是摄影机背后的人,不可以(这样做)。同样的事情,还存在于爷爷弄蜂窝煤的。一直会在角色中间纠结,很难两全。很多事情觉得自己挺狠的,爷爷对于我的拍摄是一种完全不知情的状态,是完全真实的。但爷爷作为家中的权威,很少会愿意在小辈面前流露情绪。为了拍摄主人公情感的真实时刻,就只能狠下心来。对于爷爷摸摸索索的盲人日常,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当用摄影机来记录时,才知道爷爷这一辈子的辛酸。
Q:片名叫《父亲》,导演是怎样看待爷爷和父亲之间的感情?
A:像大多数的中国家庭,这种情感一定是内敛的。能感受到父亲对爷爷的关爱,爷爷对父亲的在乎。父亲一直知道我在拍,但是不知道我在拍什么。直到爷爷葬礼上,父亲第一次看到我拍的东西,父亲眼里的泪水是对爷爷情感的外露。爷爷临终时,爷爷叫着往日不会叫的父亲的小名,父亲大大咧咧的性格却那么细心的照顾爷爷
展播时间:10月24日10:00
南山校区北苑报告厅
嘉宾:邓伟(本片导演)、黄骥(导演)
主持:苏七七

苏七七:导演本身是央美毕业,我了解之前导演做的一些实验短片,但是《父亲》这部片子又很朴实 、从内心经验出发。您是怎么想做这部纪录片的?
邓伟: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做一部多么成功、完整的片子,创作《父亲》最原始的初衷是刚好研三给了我一年的时间可以创作,同时我一直认为我家中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回家的一次经历让我确定这个想法:回家那天是一个深秋的下午,蒙蒙细雨,我的父亲就站在工地面前焦头烂额的处理一些他的工程琐事,我当时就被那个画面吸引了,那一刻就觉得也许这个片子真的能成。 我从初中就离开湖南老家去外面求学,一直念到研究生,在北京待了十几年,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少。所以创作的那段时间我也特别有感触,陪伴自己的亲人的同时也可以做自己的作品,这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是最幸福的时刻。那段时间我非常沉静,拍下了大量素材。
黄骥:我自己也是湖南人,同时你的父亲的很多经历,我父亲也曾经做过。很多湖南人会到广东深圳或者就在自己家乡做各种各样的工程,有些人做得比较顺利,而另一部分就会像导演片中的父亲一样,这些让我看的感觉还蛮熟悉的。
苏七七:我在想为什么会产生一种黄骥导演和邓伟导演创作倾向非常相似的感觉,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你们都拍到了一种城市化进程,包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中那些个体的命运和境遇,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命运,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是相通的。另外是拍摄过程中导演身份的问题,当你在一开始拍这个片子时,爷爷和父亲都抱着和孩子相聚的这种亲密愉快的心情,也有成为一个受孩子重视的被记录者的感觉,这是一开始的摄影机的意义。但是当这些家庭的变故发生,亲人离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摄影机又意味着什么?
邓伟:我虽然说和爷爷他相处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亲人之间的这种情感是一直在的,我也看出来他其实是非常需要陪伴的,拍摄过程中那种陪伴对于他和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我能在爷爷最后的这段时光这样陪着他。父亲被抓、爷爷去世的一段时间其实有一些镜头我自己是没有拍的,那时摄影机真的变得很沉重,我要做一个孙子、儿子应该做的事情,那段时间我根本没法再去客观的作为一个创作者去拍摄。其实到了拍摄后期,我觉得至少摄像机对于我们三代人的关系,它会形成一个关联,用镜头建构了我们之间的一种新的联系。
苏七七:那我谈一下我对于两个片段的感受,一个是纪录片中我觉得非常动人的爷爷唱歌的段落,我觉得这一段可能很多观众都和我一样,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时出于一个电影人的敏感,我会去想这个时候被拍摄者是否知道摄影机的在场。另一个段落是父亲被拘留,我觉得这时候你的身份是双重的,摄影机还在拍,但是你接下来问爸爸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创作者和儿子的身份在这时就重叠了。
黄骥:因为导演的爷爷是盲人,他看不见很多的东西,但他能用听觉去感受,而正好就是因为您摄影机对他时光的记录,让一位盲人的情绪通过您的摄影机被我们看见,我觉得此时这种看见和被看见就体现了拍摄的意义。我最近也一直在跟一些朋友讨论,创作者尤其是纪录片创作者,他应该怎样去处理自己的主观和客观,怎样让自己的主体性出现或不出现,因为尤其是拍自己的家人是很难的,我们作为观众有时也不知道要从哪个角度去跟随导演观看,是一个创作者的角色,还是一个家人和亲人的角色。我很好奇你怎么处理这两个身份的。
邓伟:其实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一直是纠结的,两个身份纠缠在一起。特别是在拍摄的时候,其实遇到很多情况时你必须保持冷漠,做一个旁观者对我内心来说也是挺煎熬的。包括为什么这个片子从18年拍完之后一直到现在才完成,其实也跟后期的身份纠结有关,我虽然知道我爷爷是个盲人,但是我已经习惯了,我习惯了他是以这种触摸的方式去生活,也习惯他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于是反而就形成了一种习以为常或者忽视。而当我真正的去拍摄时,包括那么多特写,我发现这些镜头才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爷爷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很多时候我就会很触动。特别是爷爷过世之后,我再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触动其实是很大的,非常难继续做下去,所以这个片子其实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
黄骥:我觉得纪录片有时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距离还是很重要的,这个距离有时首先是导演自己来决定的。因为摄影机有时就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理由,当我们没有工具和这个理由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选择把我们的目光投注在对方身上,但是当我们拿起了这个工具,它就会促使让我们的目光就投射在被拍摄对象身上,被拍摄对象因此也就会获得了一种关注。可能平时没有人会这么长时间的凝视他,但因为导演拿起了摄像机,他就变成了这个摄影机世界时空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角色,存在感在这个时候成立。
苏七七:是的,然后这个纪录片我觉得它带给我们非常巨大的共情和启发,我们可以只从叙事和人物的角度去反观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想法,也可以在座的更专业一些的观众去思考摄影机记录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场意义很大的讨论,谢谢导演和嘉宾带来这么深入且坦诚的交流。

《父亲》预告片
本文部分信息转载自边渡where space

IDF·重磅 | “IDF提名”入围片单公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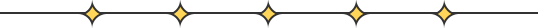





 浙公网安备 33010202002558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20200255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