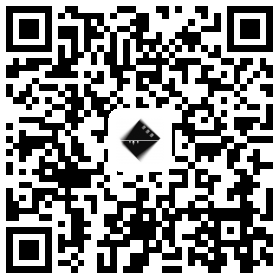父亲
Father
中国|97分钟
*亚洲首映 Asian Premiere

导演:邓伟


南山校区北苑报告厅
嘉宾:邓伟(本片导演)、黄骥(导演)
主持:苏七七
苏七七:导演本身是央美毕业,我了解之前导演做的一些实验短片,但是《父亲》这部片子又很朴实 、从内心经验出发。您是怎么想做这部影片的?
邓伟: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做一部多么成功、完整的片子,创作《父亲》最原始的初衷是刚好研三给了我一年的时间可以创作,同时我一直认为我家中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回家的一次经历让我确定这个想法:回家那天是一个深秋的下午,蒙蒙细雨,我的父亲就站在工地面前焦头烂额的处理一些他的工程琐事,我当时就被那个画面吸引了,那一刻就觉得也许这个片子真的能成。
我从初中就离开湖南老家去外面求学,一直念到研究生,在北京待了十几年,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少。所以创作的那段时间我也特别有感触,陪伴自己的亲人的同时也可以做自己的作品,这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是最幸福的时刻。那段时间我非常沉静,拍下了大量素材。
黄骥:我自己也是湖南人,同时你的父亲的很多经历,我父亲也曾经做过。很多湖南人会到广东深圳或者就在自己家乡做各种各样的工程,有些人做得比较顺利,而另一部分就会像导演片中的父亲一样,这些让我看的感觉还蛮熟悉的。
同时我也佩服导演的勇气,因为我自己在大四的时候也拍了一个关于家人的纪录片,但是当时我家也遇到一个很严重的家庭的经济问题,我的家人也需要躲藏之类,当时我记录了那个过程,但是最后并没有勇气把剪出来。因为我当时觉得家人遇到这样的困境,而我一直拿着一个机器在旁边比较冷静的在观察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的内心是很难受的。
苏七七:我在想为什么会产生一种黄骥导演和邓伟导演创作倾向非常相似的感觉,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你们都拍到了一种城市化进程,包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中那些个体的命运和境遇,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命运,这种感觉我觉得其实是相通的。另外是拍摄过程中导演身份的问题,当你在一开始拍这个片子时,爷爷和父亲都抱着和孩子相聚的这种亲密愉快的心情,也有成为一个受孩子重视的被记录者的感觉,这是一开始的摄影机的意义。但是当这些家庭的变故发生,亲人离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摄影机又意味着什么?
邓伟:我虽然说和爷爷他相处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亲人之间的这种情感是一直在的,我也看出来他其实是非常需要陪伴的,拍摄过程中那种陪伴对于他和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我能在爷爷最后的这段时光这样陪着他。父亲被抓、爷爷去世的一段时间其实有一些镜头我自己是没有拍的,那时摄影机真的变得很沉重,我要做一个孙子、儿子应该做的事情,那段时间我根本没法再去客观的作为一个创作者去拍摄。其实到了拍摄后期,我觉得至少摄像机对于我们三代人的关系,它会形成一个关联,用镜头建构了我们之间的一种新的联系。
苏七七:那我谈一下我对于两个片段的感受,一个是影片中我觉得非常动人的爷爷唱歌的段落,我觉得这一段可能很多观众都和我一样,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时出于一个电影人的敏感,我会去想这个时候被拍摄者是否知道摄影机的在场。另一个段落是父亲被拘留,我觉得这时候你的身份是双重的,摄影机还在拍,但是你接下来问爸爸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创作者和儿子的身份在这时就重叠了。
黄骥:因为导演的爷爷是盲人,他看不见很多的东西,但他能用听觉去感受,而正好就是因为您摄影机对他时光的记录,让一位盲人的情绪通过您的摄影机被我们看见,我觉得此时这种看见和被看见就体现了拍摄的意义。我最近也一直在跟一些朋友讨论,创作者尤其是纪录片创作者,他应该怎样去处理自己的主观和客观,怎样让自己的主体性出现或不出现,因为尤其是拍自己的家人是很难的,我们作为观众有时也不知道要从哪个角度去跟随导演观看,是一个创作者的角色,还是一个家人和亲人的角色。我很好奇你怎么处理这两个身份的。
邓伟:其实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一直是纠结的,两个身份纠缠在一起。特别是在拍摄的时候,其实遇到很多情况时你必须保持冷漠,做一个旁观者对我内心来说也是挺煎熬的。包括为什么这个片子从18年拍完之后一直到现在才完成,其实也跟后期的身份纠结有关,我虽然知道我爷爷是个盲人,但是我已经习惯了,我习惯了他是以这种触摸的方式去生活,也习惯他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于是反而就形成了一种习以为常或者忽视。而当我真正的去拍摄时,包括那么多特写,我发现这些镜头才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了爷爷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很多时候我就会很触动。特别是爷爷过世之后,我再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触动其实是很大的,非常难继续做下去,所以这个片子其实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
黄骥:我觉得纪录片有时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距离还是很重要的,这个距离有时首先是导演自己来决定的。因为摄影机有时就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理由,当我们没有工具和这个理由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选择把我们的目光投注在对方身上,但是当我们拿起了这个工具,它就会促使让我们的目光就投射在被拍摄对象身上,被拍摄对象因此也就会获得了一种关注。可能平时没有人会这么长时间的凝视他,但因为导演拿起了摄像机,他就变成了这个摄影机世界时空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角色,存在感在这个时候成立。
苏七七:是的,然后这个影片我觉得它带给我们非常巨大的共情和启发,我们可以只从叙事和人物的角度去反观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想法,也可以在座的更专业一些的观众去思考摄影机记录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场意义很大的讨论,谢谢导演和嘉宾带来这么深入且坦诚的交流。
两个星球
After the Rain
中国 | 104分钟




南山校区北苑报告厅
嘉宾:范俭(导演)
主持:张侃侃
Q:我们都知道导演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做这个项目,请问您的拍摄缘起和之后的计划是什么呢?
A:其实我在08年地震之后就想去汶川进行拍摄,但因为一些因素没有及时去到那边,所以是09年春天展开的调研,秋天正式开始了拍摄。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因为这个事件是影响人一生的。我们在拍摄过程中阶段性地出了一些作品,比如2011年的《活着》,2018年的《十年:吾儿勿忘》,18年之后也接着在拍。我们拍摄的主线家庭一直是叶红梅一家,里面其他的家庭也出现在之前的作品中过,但冉冉这个家庭之前没有出现过,所以在《两个星球》里是时间跨度最长的。我们会在不同阶段选择适合的内容和形式去呈现影片,有些内容适合以短篇剧集的方式呈现,有些就适合放到一个长片里。地震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第三部长片。
Q:我注意到这部纪录片在影像层面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黑白的影像和梦境般的声音,请问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
A:我们这里黑白影像的安排在纪录片里的确不太常见,我自己以前也没有尝试过。其实目的就是想强制性地让大家进入一种逝者视角去感受世界。探讨生者与逝者之间的关系是这部影片的一个核心。你说到的声音也是有特别的设计,希望营造出迷幻感、梦境感、浪漫感。包括影片中有很多明明暗暗的镜头处理,都是想要表达每个家庭的亲子关系处于一种微妙的变动中,是没有变好或变坏的明确答案的,代际关系中双方的力量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儿子的力量在增长,父亲的力量在减弱。
Q:这部纪录片叫《两个星球》,从人物关系和一些台词中我感受到了“两个星球”有很多层面的指涉,请问导演自己是如何理解这个片名的呢?
A:其实我们最早的片名叫做《爱过》,这是我们在早期对于这个故事的理解。但随着对素材不断的审视,发觉了冉冉说的那句有关“两个星球”的话,它非常触动我。我突然发现影片主题有了一种跳脱家庭关系的可能性,这种距离感是我喜欢的。大家对“两个星球”具体是什么可以有很多种理解:逝者与生者、姐姐与弟弟、姐姐与妹妹等等。但我更愿意解释为,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时空维度,逝去的生命也在另一个维度存在,甚至影响了活着的生命,两个星球会产生一些引力和斥力。
无去来处
I’m So Sorry
中国香港、法国、荷兰|96分钟
*中国首映 Chinese Premiere



蝴蝶剧场
嘉宾:赵亮(导演)
主持:沈健文
Q:拍摄对象对摄像团队的到访,是怎样的反应?
A:日本的那对夫妇是偶然遇见的,就只剩了他们一家人在那里。老人还是很高兴你来关注他们的事情,很热情。切尔诺贝利有些特殊。这些老人家不愿意被安置到基辅的楼房里,还是愿意生活在自己处于三十公里禁区的家里。他们在村子里是独自生活的状态。切尔诺贝利现在有禁区参观旅游的项目,有时也有记者团项目,我就是跟着其中一个记者团去的。我等着大家离开后,一切都安静下来,老人独处时候的状态。
Q:每一次拍摄都能得到许可吗?尤其是一部分核禁区。
A:提前申请。有些地方要申请好几个月。福岛最核心爆炸地区和切尔诺贝利四号爆炸的地方都没能申请进去,有些想拍摄的东西也没能拍到。荷兰的那个一年就开放两次,也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才申请到。
Q:是什么原因,让导演想以这样的主题去创作纪录片?
A:选题是挺重要的,在什么时间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是需要机遇和思考的。我的家乡在丹东,中朝边境上。2017年我在丹东调研时,吊灯电扇和楼屋都在抖,我们都以为地震了。后来通过媒体才知道,是朝鲜第六次核试验。从那次之后,我开始关注核电。福岛和切尔诺贝利让我在画面上认为,这个主题是值得去做的。再往下调研,它还有现实的处境。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力发展核电,这看起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可是许多老百姓都不知道核的潜在问题。
Q:整部纪录片中有许多充满意涵和细节的声音。请问导演在声音上是如何去设计的?
A:每一部纪录片,多一个元素少一个元素,他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态,另外一个作品。这是作者自己根据需要去做的选择。和混音师、作曲讨论主题时,我特别需要关于“核”的声音设计。盖革表是很重要的一个声音,用于凸显主题。核粒子冲击盖革表发出的声音,是无法模拟的,也无法通过拟音来模仿。这是真正的纪录片才会有的声音。设定这样的声音来贯穿全片,让你感觉到辐射隐隐地如幽灵一般存在。在旁白的设计上,我让当地的演员进行配音。从诺贝尔奖作品《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节选适合人物的话语,通过拼贴的方式来表达。
Q:您之前说为了作品效果,翻译并不在场。那么,导演您是如何与拍摄对象进行交流的,是手势吗?
A:我基本不打扰他们,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会尽量小声,甚至我会出去,就让他(她)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我不用他(她)做什么,他(她)做什么都好。我不需要与拍摄对象再去交流培养什么。我有论点在先,我只需要去寻找我需要的论据。
涅墨西斯
Nemesis
瑞士|131分钟
*中国首映 Chinese Premi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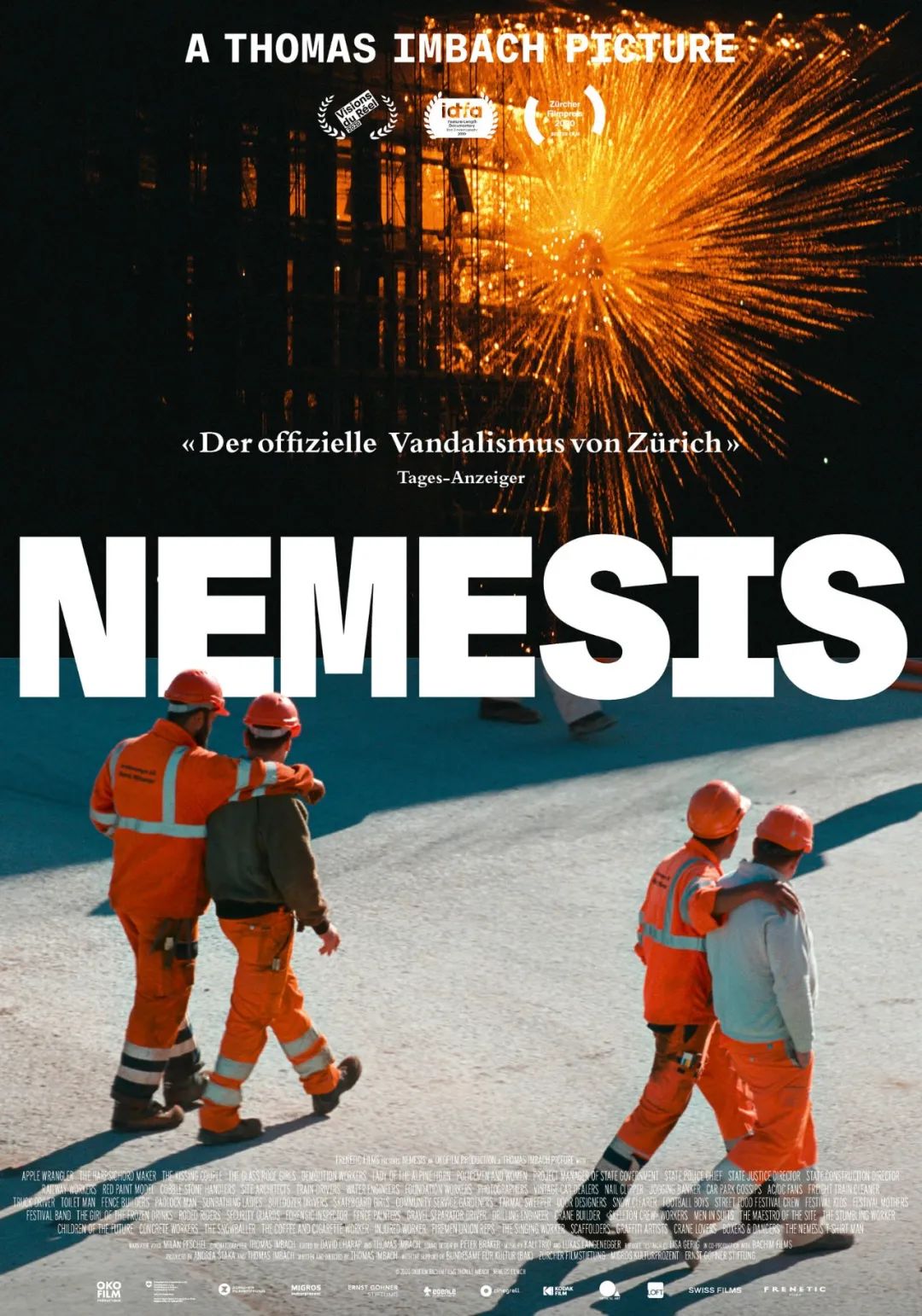


南山校区北苑报告厅
嘉宾:托马斯·因巴赫(导演)
主持:韩程
Q:导演您好,我注意到您影片中的快动作部分具有动画特质,请问您是怎样完成这部分的?
A:我主要是在拍摄过程中直接完成。在这部分我使用35mm机器进行降格的拍摄,只有在窗口向外拍摄这一个视角,这并不是在后期完成的。
Q:那么对于仅从窗口一个角度向外进行拍摄的做法,您是怎样考虑的?
A:其实我在2011年《白日已尽》(Day Is Gone)这部影片中就已经使用过在窗口一个角度进行拍摄的这个方式,但《白日已尽》(Day Is Gone)中还增有在窗口向内拍摄的视角,对窗外的画面进行解释。拍摄《涅墨西斯》缘起是我痛心于政府决定拆除我家旁边的这个旧货运站,建立监狱和警局中心,我感到有这样一个责任,也自发的想去记录这样的过程,于是用了七年时间进行拍摄。
Q:请问您是怎样完成环境收音这部分的工作?
A:其实我在拍摄过程中主要关注的是拍摄画面,其次再考虑其他的因素。当然关于配音我也有提前搜集一些声音素材,但总体来片中的配音基本是通过后期实现。这个影片本身是纪录片,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把当作是剧情片,所以影片配音上做了一些情绪化处理。
Q:导演您好,我感受到影片最后部分旁白中的难民故事和视觉效果非常契合,请问您这部分是怎么处理的?
A:首先关于难民的议题,这些故事在我脑海里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也一直会考虑在影像中如何配合这些故事,需要什么画面。其实拍摄过程中除了拆除屋顶的情节需要一直跟进拍摄,其他的时间我更多是听到、闻到,感知到窗外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时才随机开始拍摄。
山寨屏幕
Shānzhài Screens
法国|23分钟
*亚洲首映 Asian Premiere



南山校区学术报告厅
嘉宾:保罗·海因茨(导演)
主持:杨婷轩
Q:您是如何想到要去到深圳拍摄这样一个纪录片的?
A:其实我最开始是在做一个关于临时工的短片,那部片子涉及到了一些没有合同的工人的劳动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片中这位批量画梵高作品的男生。我和他加了微信之后有了更深入的交流,对他的生活非常感兴趣,于是我决定前往深圳大芬村住了两个月,看看那里会有什么故事发生。
Q:想听听导演是如何构思关于纪录片声音的?
A:在我看来,深圳这个地方整体上是很嘈杂的,所以我就先试着录尽量多的环境音,最后在素材中去选择,一层一层精简下来放在影片中。所以大家看到了很多声画不同步的处理,也都是经过我的思考和编排的。
Q:片中出现了很多“屏幕”,这些“屏幕”的设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会把本片第一场戏设计成虚构的呢?
A:当我来到中国后,我对这里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感到特别震惊,我发现人们都很依赖手机,大芬村的工人之间的沟通也主要是用微信,这让我觉得人们都处于一个自我隔离和孤独的状态中。所以我专门在影片的呈现中选择了很多微信聊天的屏幕去呈现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同时我也希望能鼓励到这些人多去表达自己。第一场戏之所以这样设置,也是我希望以一个比较典型的场景来展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因为这是我的短片第一次参加展播活动,所以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后一个段落的设计。最后我之所以要拍摄一位3D艺术家,是我认为整个世界正在数码化,我们看待艺术的方式也在数码化。同时将他放在影片结尾,也算是完成了男主角想触碰新的绘画技术的梦。
欢墟
The Mountains Sing
中国、德国 | 40分钟



南山校区学术报告厅
嘉宾:杨潇(导演)
主持:黄豆豆
Q:我知道导演参与了很多剧情片的创作,是怎么想到要拍这样一个纪录片呢?
A:其实我一直想要用纪录片的方式拍老家的山歌,我自己对纪录片拍摄也一直有向往。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剧情电影制作中我很喜欢和很多群众演员打交道,他们其实都是焦点之外的人,但是这些平凡的人都是很值得被拍摄的。同时,纪录片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去尝试自己的想法,纪录片拍摄也很自由,我们剧组就三个人,受到的制约很小。
Q:我很喜欢片中的歌曲,包括曲调和歌词。关于这些歌曲导演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A:我在喜欢电影之前是喜欢音乐的,我和当地音乐人关系很好。大家能听出其中有山歌和雷鬼的结合,也是我发现山歌不会消亡,而是以和别的东西融合的方式在不断流变。关于山歌有几点要介绍的,首先这些山歌都是完全根据场地的气氛和人物的性格即兴而来的,是瞬间的,也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每首歌曲的词是不同的。但大家听到的旋律差不多,这是因为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固定的调子,不同的调子代表不同的地域空间。我们在制作的时候,会在字幕上对歌词进行一些调整,因为壮族的语法和我们不一样,所以最后做了一定的汉化。我主要是参考白先勇先生的文学语言风格来进行调整的,因为他是广西人,文学语言又比较混杂。
Q:片中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飞机?导演有什么意图?
A:这是因为我的家乡新建了一个机场,那个机场在山顶,它被评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地。我觉得家园变成机场,山民们的生活和感知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想在我的纪录片中有所体现。
远东各各他
Far Eastern Golgotha
俄罗斯|85分钟
*亚洲首映 Asian Premiere



象山校区3号楼小剧场
嘉宾:茱莉娅·塞尔吉娜(本片导演)
主持:陆颖
Q:导演是远东当地人吗?纪录片中最后出现的海是在哪里拍摄的?
A:不是的,我住在莫斯科,但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我在远东地区居住了两年。纪录片最后部分出现的海是日本的一个海域,我们在拍摄中途带着维克多与他的妻子去看了大海,维克多与妻子从来没有去过海边。把这组镜头放在纪录片结尾是因为整部纪录片的基调有些压抑,我在最后想要有一些光明的呈现。
Q:导演在拍摄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是什么?
A:主要遇到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在拍摄的前期我们与维克多联系的过程中是很困难的;另外,在去远东拍摄的途中我们遇到了很多警察,由于地区管制,我们的拍摄受到一些阻碍。最后,资金也是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我们的拍摄得到了文化机构的少量资助,但是在拍摄过程中资金的耗费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Q:纪录片中有不少非常幽默化的当地俚语表达,并且穿插了精彩的摇滚配乐,您安排这些视听元素的初衷是什么?
A:这些幽默的俚语都是远东地区本土的语言表达,这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语言可以缓解和柔化纪录片的总体基调。片中出现的摇滚乐是维克多的歌单,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些音乐都是他平时在车上经常会听的。
Q:导演是如何接触到维克多这样一个人,并想要拍摄这样一个题材?
A:决定拍摄维克多这个人其实是完全偶然的一个契机。我之前在油管上浏览信息的时候,无意间点开了一个直播推送,通过直播发现了维克多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我觉得可以是一个有意思的影片人物。所以,就完成了这样一个作品。
1970
1970
波兰|70分钟
*亚洲首映 Asian Premiere




象山校区4号楼205放映厅
嘉宾:托马斯·沃尔斯基(本片导演)
主持:杨欣茹
Q:纪录片中的黑白色调和彩色的对比有什么用意吗?
A:关于色彩,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好,我让动画制作人先做成彩色的,最后剪辑阶段再决定用彩色还是黑白,所以我一开始还是用彩色拍摄。我将这两种色彩形式都进行了尝试,最后发现黑白和彩色的对比反而能够呈现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比,彩色是权力者的世界,黑白是工人阶级的色调,我还担心这样可能会不太搭配,最后我发现这两个色彩的结合其实更能够呈现出来他们两个阶层之间的对比。
Q:关于动画的定格技巧您是如何完成的?
A:刚开始的时候,绝大部分玩偶静止的镜头、摄像机移动的镜头都是我来拍摄的,另一些动态的画面(吃东西,接电话)是交给动画师去完成的,因为这些是必然要做出动态效果的。
Q:您是从什么渠道获取的这一段录音资料?
A:我之前在拍一部作品,叫做《一个普通的国家》(An Ordinary Country),我的想法是通过录像的方式来展示波兰,所以当我挖掘档案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机构收集从1945年到1989年所有的材料,包括文件、音频和视频。在1990年之后,那时因为波兰的政治变革,很多档案资料都永远的消失了,但其中一些仍然被保留下来。我在做上一部作品的时候发现了这一段60个小时的录音文件,很少有这么长时间的录音素材,这是非常珍贵的。这些录音档案包含了这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已经足够让这部纪录片完整,所以这我决定把这60小时的录音文件当做我这部纪录片的起点。
Q:您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之后是怎么解决的?
A:首先,在当时我有了录音档案之后,我尝试着对影像和录音进行处理。在1970年想要得到照片是非常容易的,但那个时候我无法对它们进行组合。困惑我的是,应该依据录音来剪辑,还是依据影像去剪辑?它们二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其次,我花了三年的时间在做这个纪录片,但是在纪录片完成的前半年,我突然被通知要参加一个比较重要的电视台周年活动,所以我必须在活动开始前完成这部作品的制作。
Q:如果有充分的时间,您会怎么完善你的这部纪录片?您是否有想过加入在这段历史中受其影响的知识分子?
A: 我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如果我有更多的资金,我可能会增加更多动画的部分。第二,因为我无法得到更多1970年代的移动影像的素材,所以没有办法如你所说加入其他知识分子的影像资料。而且在波兰,已经有很多有关这场抗争的作品,但是大多是从受害者的视角出发的,很少从政治家的角度和档案材料出发,所以我想聚焦政治家这样不同的视角进行呈现。
Q:导演有想过把这部纪录片做成一部剧情片吗?
A:讲实话,我没有想过把它做成一部剧情片,我认为相关的剧情片已经很多了,用动画的方式去呈现不算很经典,在数量上还是比较少的。并且在我看来这部纪录片最有力量的部分就是这段录音,如果纪录片脱离了真实的录音片段,就失去了它的力量。
孤注
ALL IN
中国 | 97分钟




南山校区学术报告厅
嘉宾:周浩(本片导演)、李博(本片剪辑)、
黎小锋(学者、导演)、姜娟(学者)
主持:余雅琴
余雅琴:请问导演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缘起是什么?
周浩:是派华影业公司联系我拍摄一个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纪录片,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个群体。然后我根据他们提供的十个拍摄对象,选择了现在的两个进行拍摄,又因为各种机缘让此片形成了现在的形态。
余雅琴:剪辑师能否与我们分享下剪辑过程中有意思的事?
李博:其实我从调研阶段就进入了团队,后来我们也是一边拍摄一边整理素材,大家现在看到的结构是边拍边讨论出来的。我们最初有三位主人公,后来剪掉了一位我们认为可能比较符号化的。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考虑放入导演,但随着拍摄的推进,我们发现由于拍摄对象的背景比较特殊,摄制组对他们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于是我们在后期慢慢加入了两个人物和摄制组之间的关系,最后就成了现在这样。
黎小锋:其实我算是看着周浩导演成长的,也是见证了他的作品难度越来越大。《孤注》是一部关于抑郁的纪录片,难度又更大了,有关这个群体的纪录片是很难能拍好的。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个难度很大的纪录片来说,确定一个结构和主题是非常核心的,导演是在素材积累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开始剪辑的?
周浩:大概拍摄到两三个月的时候。
李博:我拿到了几十个小时的素材之后,就开始了粗剪。
姜娟:我看了这部片其实情绪很难平复下来,很敬佩导演团队的创作。我想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决定把自己放进去的?
李博:其实我们每天拍完回来都会开会一起讨论素材、分享各自的感受,然后逐渐发现人物和导演组的互动很有意思、很复杂,所以是在拍摄期间就有了这个想法,最后在剪辑的时候完成了它。周浩:我开始当然是想作为旁观者拍摄纪录片,但是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告诉摄影师要把自己的团队拍摄进去。因为我发现随着事态发展,如果没有我们自己,很多故事就是不成立的。这也是受到多年来积累的经验的指引吧,比如我也很直接地感受到他们即将要拒绝我们的拍摄了,所以我在最后一场戏之前告诉了团队,然后最后一场戏也拍得很顺利。
黎小锋:这次拍摄这个主题的内容难度在哪里?又如何面对其他时候拍摄对象拒绝拍摄的情况?
周浩:其实我面对每一个题目时都是如履薄冰的,每一部片子都有它的难度。在人物方面,这部纪录片中的两个人都是一开始就同意被拍摄,非常勇敢,做好了把伤口拿给大家看的准备的、希望为这个群体代言的人,所以我也很幸运。另外,大家能看到的是成功的案例,那么背后当然有很多不成功的案例。那些素材就放在那里,我想有合适的时机再继续做吧。我记得一位国外的纪录片导演讲过——从来没有一部片子值得你付出生命,所以其实做不了是很正常的,那就换下一个题目,我们都是生活在不确定中。在这里也预告一下,我在年底会有另一个片子《武汉工厂》出来,粗剪已经完成。这部片子就是在讲述某种不确定性,我觉得未来的生活方式可能就是在不确定性中去寻找确定性。
可怕的孩子们
Les Enfants Terribles
法国、土耳其、德国|89分钟
*中国首映 Chinese Premiere



象山校区4号楼205放映厅
嘉宾:艾哈迈德·内杰代特·楚普尔(本片导演)
主持:杨欣茹
Q:您拍摄这部以家庭为主题的纪录片的契机是什么?
A:作为一名纪录片制作人,同样也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开始出去工作,在不同国家工作的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我发现在我妹妹身上发生的事情(想要离开村庄),20年前在我身上也同样发生过。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价值是可以被所有的人理解的,这个问题是在全世界都有发生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想要去追寻自由,这也是我想要去拍摄这部作品的原因,也是由于妹妹的这件事情,我才真正进入到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我意识到我可以告诉他们,每一代人都享有自由的权利。
Q:您是自身比较关注女性议题还是由于家庭中女性形象比较独特才决定去拍摄呢?
A:因为我从小在一个大家庭长大,有叔叔婶婶还有很多小朋友。我在小的时候对男女性别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直到青少年时期才慢慢意识到差异。我们无法忽视人类之间的不平等,只是我的妹妹更早意识到这种不公平现象的存在,这些意识到不平等问题的女孩们才能去争取她们的位置。我猜我的弟媳也面临了这样的不公正,但是我尝试从我的弟弟的角度来表现他们年轻一代人的婚姻关系。我的弟弟作为新一代的人,同样也在传统和现代中面临问题。所以我希望在纪录片里面表现出来其实是平等的,并没有想要强调男女其中的一方,我只是忠实的去记录了他们的故事,如果他们其中一方的分量在故事中比较少,那也是他们的故事,不是我的。
Q:你认为摄影机的介入是否会影响到妹妹的想法?
A:刚开始的时候我同样拍了家里的表兄弟和其他人,我也想要去帮助家里的其他亲戚,在这些人里面,我的妹妹似乎是更能够意识到问题的一个人。如果我的家人或者邻居意识到她们的生活有问题,比如我的爸爸妈妈,我并不能够改变他们的想法。现在世界正在改变,我认为我的妹妹能够改变更多人,因为她和大多数人的情况是一样的。我认为我的弟弟也非常重要,弟弟认为不需要用太激进的方式进行改变,他不希望破坏原有的传统。所以这两个角色在纪录片中形成了一种平衡关系,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Q:你的父母看了这部纪录片吗,他们有怎样的感受?你会继续拍摄下去吗?
A:我没有给父母看过,但我给妹妹和弟弟看了这部片子,他们非常激动,这让他们回忆起了之前的生活,我在土耳其只放过预告片,我想一旦我的妹妹离开了我们的村庄,我就会把这部纪录片放给我的爸爸看,因为我害怕爸爸因为生气而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阻止妹妹离开这个小村庄。虽然每部纪录片的拍摄都会经历种种困难,但我从来没想过拍家庭也会这么困难,整个拍摄过程很挣扎,很痛苦。我没办法再回到村庄里继续拍摄,但如果我的妹妹出去读书或者有其他发展的话,我可能会跟随妹妹继续拍摄。
Q:为什么起名叫《可怕的孩子们》,而不是《可怕的父母》或者其他?
A:它是法语中的一个概念,在法语中并不是“可怕的”的含义,而是指的孩子们想要创造自己的世界,但他们被围墙包围了,他们需要离开那些围墙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它在法语中有一个很好的含义,我不确定我是否应该将它翻译成英文(笑)。
男人和他的摄影机
A Man and a Camera
荷兰 | 64分钟
*中国首映 Chinese Premi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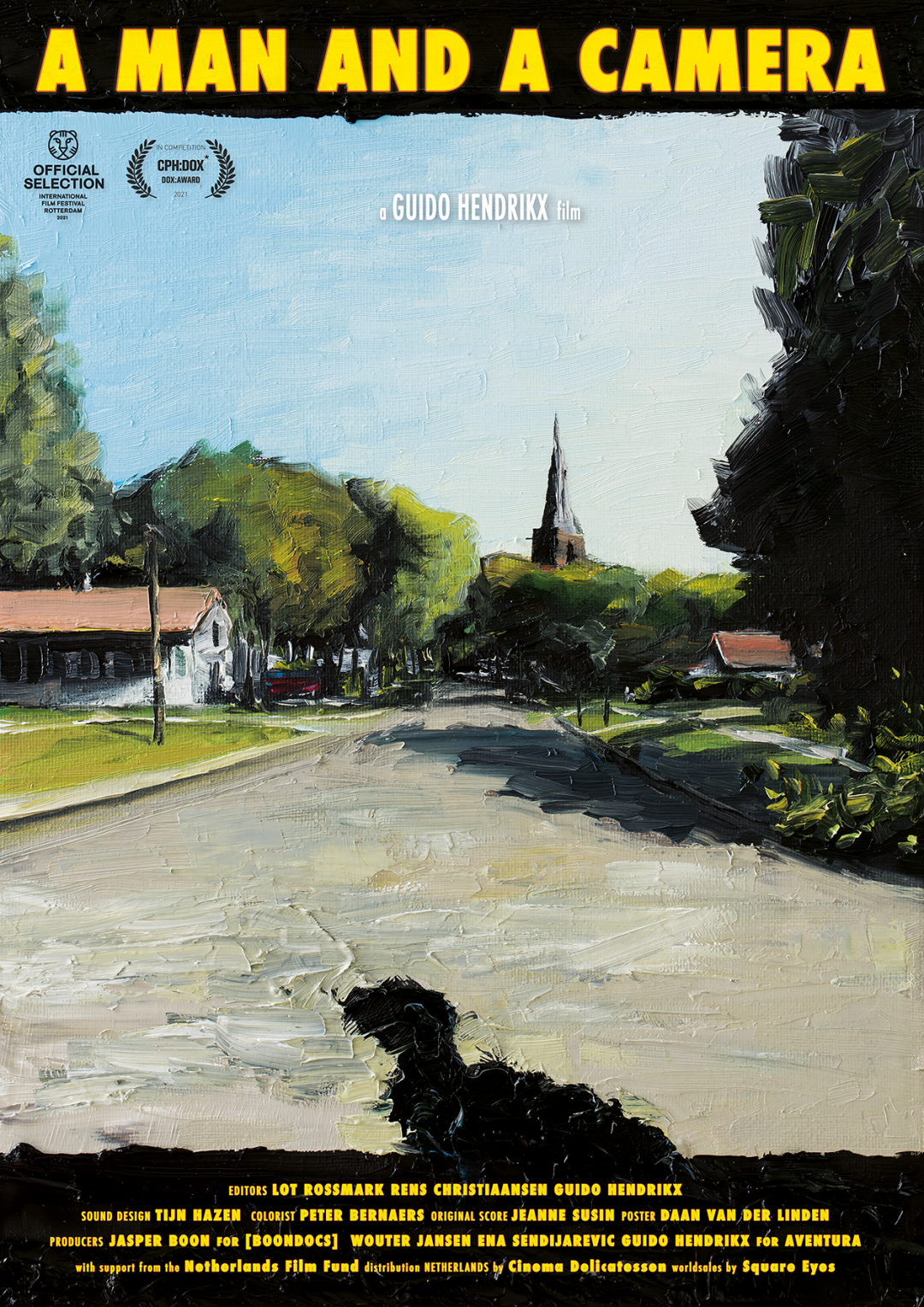



蝴蝶剧场
嘉宾:吉多·亨德里克斯(本片导演)
主持:沈健文
Q:拍摄过程中是否有一定的风险?拍摄过程中拜访对象的区域有多大?
A:拍摄过程中有遇到一些阻碍,就像在片中所看到的那样我们遇到了警察。主要是在城郊进行拍摄,那边的人们对纪录片和镜头并不熟悉。我将自己局限在那个范围里进行拍摄。在定剪之后,我们对所有拍摄对象进行了回访并请求许可,在最终的播放版本中,所有出现的人都获得了许可。
Q:拍摄过程中,导演将自己的互动设定在了何种程度?
A:在拍摄之初,当别人问我是不是某个频道的,我会点头回应。但后来我发现这不符合我所需要的效果。我给自己设定了三条规则:1、不说话,也不点头摇头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以防破坏紧张感;2、门一旦打开之后,就由被拍摄者决定何时开始,何时结束。3、只去拍摄普通人和普通的生活场景。我可能会微笑,但这个取决于被拍摄对象的态度。如果被拍摄者对我微笑,我也会镜像地微笑。但也仅止于此,不会再给更多的反应。
Q: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来表现?
A:我制作这部作品有多个缘由,一方面是对人类行为的好奇,另一方面也想对影像媒介有所探索。我想做的作品不仅有对人类行为和人性的探索,在影像上也想要有所创新。在我看到的作品之中,有的作品探索了很了不起的主题,但是制作手法却很普通。我看到的作品有99%都在拍摄明星、边缘人群、亚文化群体等,而我想要做一部关于普通人的不平凡影像。这些思考让我在探索“怎样使用摄影机”这条路上走下去,“我们到底能不能信任陌生人”这个问题也在驱使着我继续走下去。
Q:这部作品带有一定冒犯性,甚至会让被拍摄者感到恐惧或害怕。导演怎么看待自己可能会给别人带来的情绪冲击?是否在某种情况下,导演会放下自己的原则,向被拍摄者解释自己的行为?
A:每一次敲门,就像是一场赌博。在一开始时,我还是有些挣扎的。在做这部片子过程中,脑子里始终有两种声音,一个是不断在问自己“我把我自己放在了什么样的境地,自己在以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方式示人”;另一个声音在说“我这样的坚持是对的,打破了制作纪录片的条条框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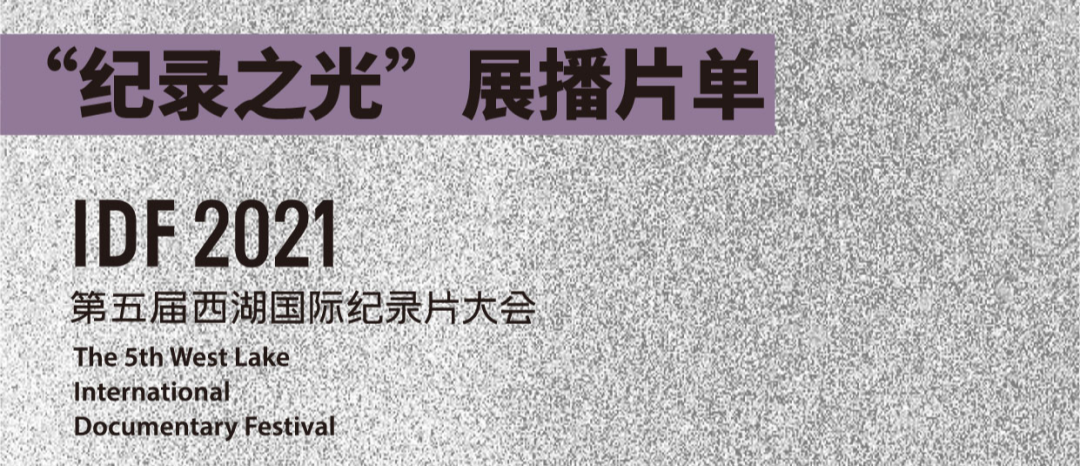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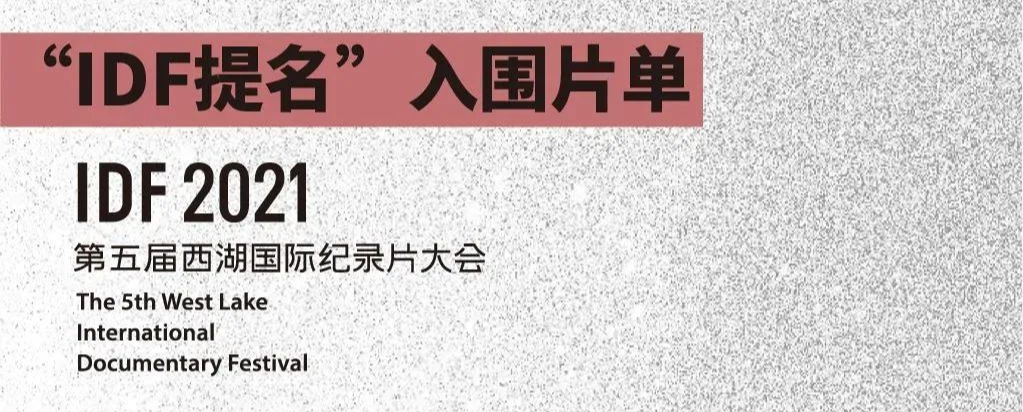
IDF·重磅 | “IDF提名”入围片单公布

 浙公网安备 33010202002558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20200255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