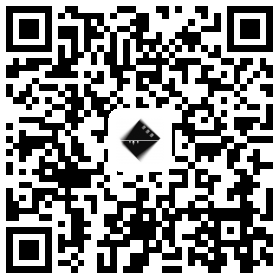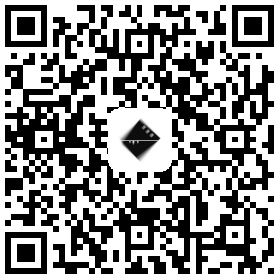第五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 The 5th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简称“IDF2021”)是由浙江省广播电视局与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国际专业纪录片盛会,是集纪录片推优、提案展播、论坛、工作坊于一体的高品质人文艺术平台,本届年度主题为“感·知”,于2021年10月22日-25日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












QA集锦
Q:如何理解记忆让渡这一概念?如何在不同的记忆载体,例如崔洪钗的文字性记忆与当代的影像动态影像记忆之间进行切换?
「张侃侃」A:记忆让渡的“让渡”一开始是财产的概念。无论是崔洪钗的亲人把它卖到市场上,还是在更大的社会文化层面上,把记忆让给博物馆或美术馆,这都是一种让渡行为,都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让记忆去流动,甚至去变形。有一个跨媒体的概念。我们日常接触的多媒体有静态的文字形象,也有动态的影像形象,他们以一种非常复杂且难以解释的生理神经功能去影响我们的记忆。完全用静态影像构成的电影,放慢放快也是逐格的静态影像。刚才我提到了内在文字的概念,我们看影像时也会受到思维、文字的影响,巴特、本雅明都觉得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破解它。特别有用的是德里达写作学的概念,它将文字时代与影像时代区分开来,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要做思考一下。因为刚才崔洪钗不仅在看电影,同时也包含各种各样的生活经验,这种记忆是多媒体的,只不过现在我们能用到的或是能变成个人记忆的,只剩下日记本里的影像目录了。
Q:在一个后理论的时代中,能否还是利用理论来看待我们对于记忆的处理?我们能否信任我们身体所给予我们的记忆能力,借用技术成为赛博格后再去进行回忆呢?
「张侃侃」A:的确我们的记忆会受到某种主流叙事的影响,我们记忆的也不是全是自己的记忆,比如在工厂劳作形成的肌肉记忆。另外,我们在话剧、电影中的表演即兴,也是有表演方法借助到肌肉记忆。您提出的问题特别好,个人记忆是与更大的公共记忆、集体记忆掺合在一起的。但个人记忆没有必要必须变成集体记忆和大众记忆,抗争的层面就存在这里面。
「主持人谭政」A:媒介是人的延伸,社会向前发展,肯定自然而然需要借助各种技术帮助人进行记忆、适应和改造这个社会。我们不应该排斥和抵制技术,就像艺术研究、理论研究一样,在数字人文之后,接触和呈现的东西都比当初多得多,现在影像体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会造成准赛博格的东西,这是历史的必然。
Q:在有关真实与记忆的探讨中,作为创作者,在前期可以做些什么准备让感知和呈现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呢?
「赵一工」A:这并不完全归属于前期的准备。访谈中的人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假如这个人的声音悦耳,表达能力很强,就容易吸引你;但是表达能力较弱的、甚至不愿接受采访的人的言说也很重要。现如今信息量和证据都都变得更多、变得有好有坏,我们也迎来了选择的困难,也无法确定所谓更接近的事实。人的动机问题也要算为真实的一部分的话,那真实不可能是完全有形的。
Q:像我们现在处于影像丰富,记忆的大时代,那些被沉浸下去的记忆体是否有其他价值,除了放在博物馆馆藏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价值?
「赵一工」A:我做老影人的口述人,这些新中国前40年里最重要的电影人,他们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那个时代的电影不比今天的电视、各种网上的视频影响力小,那时谁要是演过某部电影,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便可能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言人,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价值。即便是放在博物馆里,有一天大家要研究所谓中国电影的脉络,无论是艺术片脉络还是电影发展的脉络,他们的讲述就都会变得非常有价值。
Q:刚才谈到电影是公众无意识,就像一些特殊事件的纪录片,它们没有被纳入正片中、没有成为公众记忆的影像,难道只能成为导演的私人记忆了吗?它们有没有可能成为公众的整体记忆?
「赵一工」A:成不成为公众记忆由各种因素导致。它没有成为公众记忆,并不意味着没有作为公众记忆存在以及传播下去、流传下去的意义。我认为那些东西也有价值,如果过100年以后,人们有机会看到今天的各种情况,甚至想要找到2021年10月24日下午的一个座谈会,他们就找到了,那就很有价值。但目前这个会存在的价值是对纪录片界和对爱好它的人们的价值。






李洋教授与观众QA集锦
Q:如果一个不具备主体性的人造物,它生产不公开的内部影像,既然它不公开,只是一种推理的可能性,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是什么?您在人工、人造、想象与幻想的边界做区分,最后人工幻想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意义在哪里?
A:人工幻想就是一种推理,一些科幻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人工幻想,它生产了一种表象,这个表象是某种主体性留下的痕迹,这个主体性不指向人类,而是指向了人类无法沟通的主体性,在现实当中很难找例子,只能在科幻作品里找例子。其启示意义是真正能针对未来的,至少从想象、幻想的层面,也可以指向一种无尽的未来的可能性,也可以用这一点来研判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边界。一种绝对陌生的未来和可能性,可能是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绝对焦虑的本原。
Q:您对图像做了推演梳理,人工智能想象与图像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或启示?
A:人工想象会生产具体的客体图像,人工幻想就是你看到某种东西正在制造一种精神图像,但其实所包裹的主体完全不是人类可沟通的主体,没有任何客体的图像出现。比如那个海报制作时,人工智能是有参与的,最后结果要输出一个客体的图像,图像指向了客体图像,而幻想指向的是一种内部的,无法沟通的图像。
Q:人工想象的图像,在整个图像的思考当中是指向未来的可能?
A:我想引向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边界在于它是否有一种人工幻想,因为人工智能的自然科学对人工智能的支持性讨论,它是为人类服务的,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恐惧和害怕。什么时候到了人不能控制的时候?什么时候在可控与不可控的边界?当智能可以产生我们所赋予的主体性之外的另外一个主体性,甚至可以为自己生产一种它自己的一种幻想和精神图像时,它有了自己的欲望以及满足它自己,其实就是完全脱离了人与智能的相关性来讨论主体性时。简单来讲就是到了一个思辨实在论的讨论,完全摆脱了相关性来讨论物自身存在的可能性时,就打开了人的认知的边界。过去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认识关于这个世界所有的知识在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当中建立起来,哲学家开始尝试建立一种通过推理才能抵达新的世界存在的认识,就是思辨实在论。
主持人(周佳鹂):在您最后讲到人工幻想的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导向思辨实在论意义上的思考,有某种关联性吗?
A:我不想变成思辨实在论的某种讨论,如果通过思辨实在论来理解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大家看昆汀·梅亚苏的《有限性之后》,第一章讲的是考古发现,人造物和人性边界被推翻的问题。所以思辨实在论有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是对于人造人类文明和人自身绝对的切割。
主持人(周佳鹂):在今天纪录片大会的一个学术讲座上,我还是想请教李老师,如果在人工幻想的这一概念下,有什么样的设想在未来的影像当中?如果有一个背景和前提的话,影像自身有没有拥有人工智能的可能?
李洋:只有艺术能给答案,科学没法给答案。后人类主义是80年代提出的围绕着赛博格、生命技术、认知科学、脑科学、计算机技术、新媒体技术等一大批新技术产生的一种对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绝对影响了一种新的思潮。大家很长一段时间集中关注人工智能,后人类的一些科学现象、科学发明,我们就跟着来自科学界的新闻这样去讨论太被动了,所以人文学科在大学中不断被挤压,今天人文学科在美国被挤压得很严重。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面临类似人工智能、后人类主义,其实是由自然科学驱动的讨论,人文学者只是一个跟随者和回应者,不是主动参与这个问题讨论,且讨论时并不平等。我觉得艺术哲学和科学在历史上是平等的,是面临着对于现状的阐释和对于未来的解释,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并不是被动地回应问题。我向学生讲人工智能将来会怎样,会怎样改变艺术,我们要怎么办?这是被动回应。而主动的讨论是用艺术和哲学在历史当中曾经回答人类命运、人类技术问题的方法去回应,比如艺术、人造物、人工之物,这是一种艺术的方法。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建立平等讨论的前提。在叙事层面上,如果科学关于人工智能的新闻,科学家的理论表述,都是对于未来的叙事的话,那么它与其他的叙事是平等的,比如哲学对未来的叙事,也没有发生,但也可以对它进行解释。除了科学和哲学之外还有艺术,艺术对未来的叙事也不完全根据科学,这就是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的意义所在,它与科学有关,但绝不仅仅是科学。
人工幻想,如何认证?怎么证明人工幻想的存在?通过推理,但科学也需要推理,也需要假设,科学也需要想象,物理学家费曼说作为物理学家最重要的是imagination 的能力,坚定从想象的问题进入到人工智能的讨论。我想人工幻想只是一种推理,很多东西只能推理存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最传统的经验论是要处理我们能感知到的东西,当然科学会借助大量的光学仪器、计算仪器将不可感知的东西带入感知世界,显微镜的发明、望远镜、无人机、太空的测绘、导航都通过某种技术把不能被感知的东西通过某种方式转化为可感知物。思辨实在论提出什么东西?那些不能被转化的就不存在吗?所以感知世界之外无法被转化为可感物,可以被推理存在,但有一部分人造物可以将这种推理以故事的形式,以叙事的形式,以图像的形式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是科幻电影。科幻电影与科学家在关于未来的问题上是平等的,提供了关于未来的两种不同的叙事,艺术家的工具是imagination ,而科学家的工具是科学符号、科学实验等。
Q:您提到人工物与人造物是否存在一个次级关系,比如人制造了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又制造了一个机器,它又制造了一个机器,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人造物或人工物之间的次级的划分或内在的更次等的一连串套娃式的东西?人造物是非人也可能是无人的东西,这种东西指向主体性痕迹,或是一种虚幻的主体性,假设我们这个东西有一个思辨的起点,默认的是人或类人的生物,这里体现了一个东西,我们怎么去把握这样一个起点以及可能的东西?比如,我现在造了一个机器,你可以把机器视为一个人工物,又产了一个人工物的人工物,但我在想中间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比如克隆人,我造了一个克隆人,这是人造物还是人工物,对此我还是有点疑惑。 主体到底是从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开始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个限定性?我们是不是能抽离之前的东西,从中段找到一个东西认为是一个主体?现在将人类当做为一个起点,我们在狭隘的认知范围之内是这样认为的,是否存在一种我们可以从中段找了一个机器人,以它为主体思辨的起点往后推,是不是可能?如何解释?
A:是不是套娃式结构,高阶生产低阶物,低阶再生产次低阶物,不是这样的,主体性上是平等的。恰恰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才会想人是最高阶的,人生产了人造物,人造物又生产了人工,人造物当中又有一个人工物,所以关系是什么?人工物是人造物的一种,所以人造人,人造人也是一个人造物,但它有一种主体性,但只不过主体性是一个错觉。机器人是人造物吗?其实是人工物,因为它会说话,它有一些表象,让我感觉它在所有的人造物当中有主体性,变成了人造物当中的人工物,主体性是一个错觉,包含了它。但并不像在科幻电影当中的机器人,机器人是智能的,在欧洲哲学的背景当中我喜欢用主体性的概念,但关于主体性的讨论有一个误区,大家认为主体性是人性,但主体性不等于人性。
第二个问题,你把我所说的主体性替换成智能就好办了,通过精神影像去产生某种东西的某种智能,以及它产生某种智能的幻觉,这就可以被理解了,这就是人造物与人工物区别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你要说中段的话,完全排除一切前提,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排除一切前提的话强调一个如何判定。比如在火星捡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看上去像是某种东西制造了它,但绝对不是人造的,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类存在,在这个东西上面就体现了某种主体性的痕迹,这是一种人造物,但不是人造的,如何断定?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与自然物相比是有某种图像遭遇了再现的过程,这是一个目的的结果,而这个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影像,这个影像是一个再现的。图像作为一个再现参与了制造它的某个过程,我们来断定它是有主体性的,但这个主体性不是人,就排除了人的起点的假设。假设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但有一些物品,它是人通过某种图像以在线的方式参与了制造它的过程,这个世界也有可能存在,这是思辨实在论。
Q:图像、人工图像、人造图像都是建立在一种所谓的人的五官俱全的基础上,盲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很难达到想象,只能有幻想?对于盲人来说这个命题怎么去定义。
A:我不想视觉的问题,我认为图像与视觉是两个问题,很多人讨论视觉文化时与图像混谈,当然图像是视觉文化非常典型的对象,但你要发现如果我是一个视觉文化的对象,我不是一个图像,起码我被造出来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图像,所以图像与视觉文化是两件事,更多强调的是知觉在客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的关系问题,图像是一个真正的思辨、思想的对象。所以,图像在这个意义上是非视觉的图像,盲人脑海中的图像存在没问题。盲人在脑海当中形成精神影像,但盲人从来没有拥有过视觉。
Q:您谈到基于一个想象的图像,人再有一个行为去再现它,但纪录片拍摄过程当中是没有这个前提的,很多导演是没有任何预设和想象的,没有那个图像的画卷就去拍摄了,在这样一个与纪录片非常悖论的属性当中是否可以有连接点?
A:摄像机是一个模拟视觉的机器,但跟视觉肯定是不一样的,用一种技术将这个世界的印象保存在介质当中,这是摄像机基本的工作原理。我们去发明照相机或摄像机的目的是将这个世界保存为图像。也许一个导演在拍摄时,讨论有一个前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们需要想象吗?没有想象,这是一个哲学讨论。这个哲学讨论在哲学史上有分歧,有一派哲学家,尤其经验主义的哲学家认为我看你时是没有任何想象的参与的,因为想象是一种Recall,Recall是指物象物体以影像的反射投射过我之后存储,留下一个知觉的痕迹,这个痕迹会随着时间的延伸不断地淡化,但有一部分会成为记忆memory,但想象的是Recall的记忆,从图像当中把当时看到的样子再恢复起来,看的过程当中是没有想象,通过过去保存的所有的或深或浅的痕迹相互在发生关系。
哲学家孔狄亚克说看的时候有想象的参与,比如我们看到远处是以知觉进入到我的精神世界的,但我看得不是很具体,比如我看不清他口罩上是不是有一个图案造型,但当我视知觉达到一个区间或边界时,或是视知觉达到某一种余弦值时,我的想象会参与看见这个动作的建构,这是孔狄亚克的观点。孔狄亚克说了一个问题,正因如此,看绝对不是被动的看,看绝对有注意力,所以我们讲知觉的悬置就是知觉被建构的过程。我认为纪录片的摄影师当然是一种记录,但在纪录片领域当中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被动的如实记录,一种是参与性的。在纪录片中也有一种主体性想象,通过视觉建构的方式去介入这种理论。
Q:我们所处的时代确实处于艺术与哲学被技术牵着走的现状,这种前瞻性的,或是很有启示性的东西是不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缺乏传播与发声的渠道?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很缺少这样的途径,将艺术与哲学的力量再重新的发挥出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复现出过去时代艺术与哲学对于社会和人文精神的引导?
A:这只是一个现状,或许未来没有那么悲观,也许人文学者慢慢就会在人们认识这个问题的讨论当中获得更多的回应。但更重要的是大家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如果完全在技术驱动或科学驱动的角度上被动地追随这是错误的。哲学当中的很多假设、预设,哲学作为一种遗产,包括艺术在想象科学当中有大量的参与,这都是我们可以重新进行讨论的路径。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当代性的焦虑错觉当中,我们总觉得现在很焦虑,我们想要解决和了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被祛魅,这是当代的错觉。每个时代的人都会面临跨越式的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某种技术焦虑。你要逐渐地从焦虑当中脱敏。人总是有着一种超出技术所提供的形象生态变化所能提供的之外的需求,对于欲望本身的一种欲望,总会超出给定的东西。人工智能真正能创造艺术吗?也许,但真的能满足人吗?未必。归根结底,我们要对未来的幻想避免过度焦虑,但要相信人总是有难以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总是通过艺术来实现的,而非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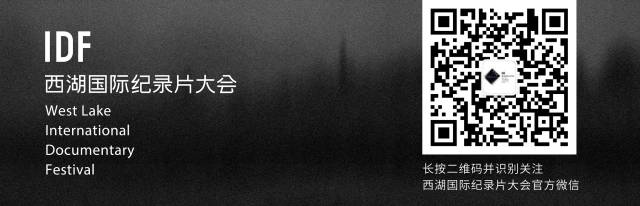
 浙公网安备 33010202002558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20200255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