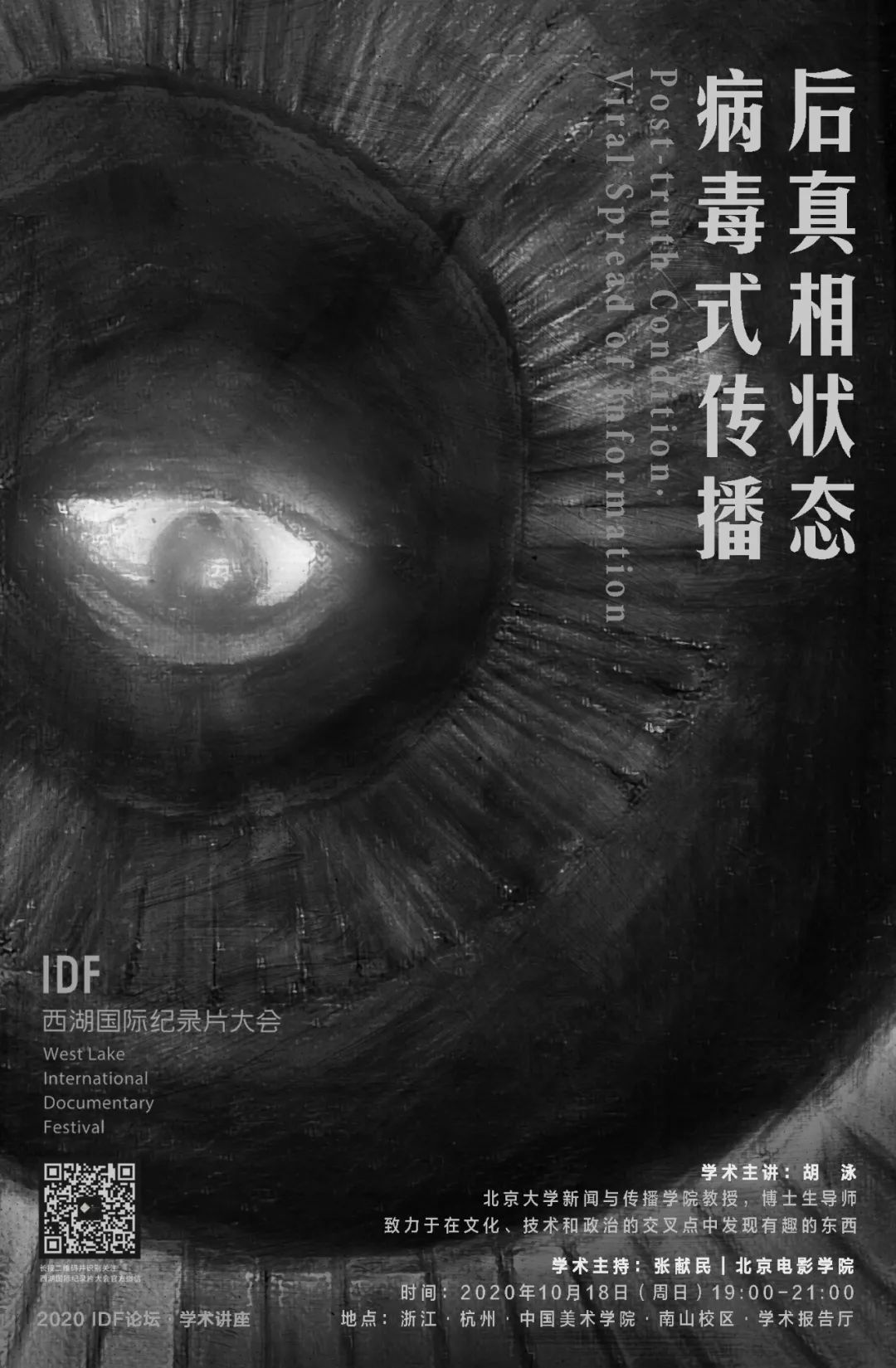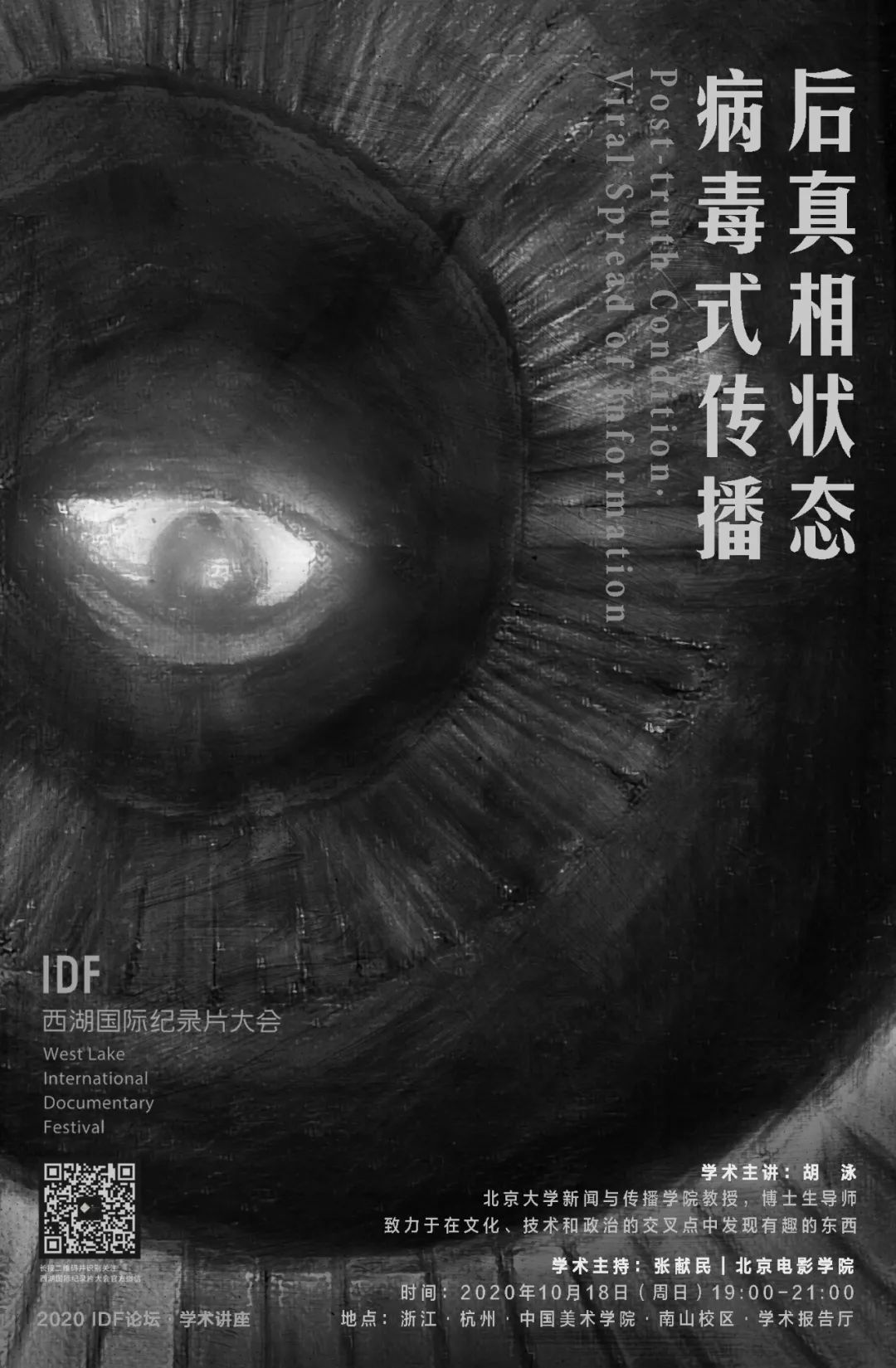IDF学术·讲座 | 胡泳——后真相状态·病毒式传播
2021-07-27
IDF学术(IDForum)是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学术版块,旨在以宽阔的视野、深度的思考,整合与更新纪录片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以此来伴随和支持纪录片创作中的艺术探索与社会实践。本届论坛学术主题为“后真相时代的影像真实”( Reality of Image in the Post-Truth Era),由学术讲座、学者论坛和作者论坛三部分构成。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华互联网研究年会(Chinese Internet Research Conference)指导委员会委员。致力于在文化、技术和政治的交叉点中发现有趣的东西,特别是解放性的文化实践,网络和网络社会理论,数字经济与管理,以及人的主体性。出版《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知识论导言》等专著。
我用了一个并列式的题目,后真相状态本身不是这两年的事情,其实从实际生活和学界的讨论当中,这个事情是起始于2016年,我们已经讨论了好几年了。“病毒式传播”是双关语,既是指传播当中的一个现象,尤其是互联网界,经常会使用“病毒式传播”这样一个说法,同时它也暗喻2020年以来,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场新冠病毒。这个新冠病毒当中有很多东西,本身既是病毒的传播,也是信息的病毒式传播,这是我的题目的一个简单说明。
我们从原始出处说起。《牛津词典》每年会评一个年度英语词汇,2016年这一年,它把post-truth这个词评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这个词非常明显地抓住了我们的时代精神。黑格尔意义上的时代精神,本质上指主宰着世界历史某一特定时代的特征,今天我们大约可以把时代精神理解为时尚的图式。
首先来看后真相的定义,这是《牛津词典》的英文定义:所谓的“后真相”,用来描述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造成更大影响的情形。我们看这里的关键词,替代客观事实的东西有两个:第一个叫情感,第二个叫个人信仰。
这个定义何以抓住了时代精神?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在大西洋的两岸,尤其在英语世界当中,这一年可能会因为“真相”变成一种滑动的概念而被后人所铭记。从这一年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趋势,就是真相已经大幅贬值。贬值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以前政治辩论的黄金标准,是看谁说出了真相,谁又歪曲了真相。到2016年以后,我们看到所谓真相变成了一堆毫无价值的残币。这是因为,后真相赋予真相“次要”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它和传统政治有很大的不同——后者虽然始终争论何为真相乃至伪造真相,至少还承认真相的重要性。
很多时候,我们要强行地给我们所经历的时代一种命名、一种定义。其实它不科学,但这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们强行把2016年称之为开始正式进入后真相政治的一年。后真相政治,可以给它一个同义词,我把它也叫做“后事实政治”。因为我们看到《牛津词典》的定义里,事实被情感和被个人信仰所代替。“事实”是我下面要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事实”实际上不仅是我所在的学科——新闻传播学经常要处理的核心的东西,同时也是纪录片影像真实所处理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即我们要追问“什么是事实”。

回到后真相时代的命名上,为什么我们在2016年要做这么一个判断?原因是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英国脱欧。英国脱欧是2016年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我们把这件事情还原到政治的场域当中。比如在英国,假定我是主张脱欧的,张献民老师主张留在欧洲,我们俩需要对英国民众的头脑进行争夺,看谁能战胜谁。那除了这两派的政治主张以外,其实还要考量它们的传播策略。我们知道最后主张脱欧的人获胜了,尽管是以一种很微妙的比例获胜的,但不管怎么样,脱欧派获胜了。主张脱欧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一件事,当然不完全是因为这一件事而成功,实际上有很多因素导致他们的成功,但从传播的角度来讲,他们做对了一件事: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而有效的口号,叫“夺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也就是说,对所有英国人宣扬,我们需要夺回英国被欧盟拿去的控制权。当然这是一个口号,这个口号需要化为具体的、能够具有说服力的东西,来证明英国人的控制权被欧盟拿走了。大家看图例里的这个标题,认为脱欧派所造的上述口号价值3.5亿英镑,即它所造的这个虚构的事实(fiction)价值3.5亿英镑。
这3.5亿英镑怎么算出来的?很简单,为了在全民公决当中获胜,脱欧阵营谎称英国每周要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这么多钱,英国人不分阶层,不分代际,一听说欧盟作为一个官僚机构可以每周从我们英国拿走3.5亿英镑,假如你是英国人你就震惊了,我们怎么可以被布鲁塞尔所控制呢?它怎么能拿走我们这么多钱?
事实上,这完全是虚构的,有相当多的事实核查者都指出来这个数字不对,但这并不妨碍脱欧派把这个标语刷得大街上到处都是,包括刷在大巴上。大家看这个经典的场景:鲍里斯·约翰逊和特蕾莎·梅,你看后面背景上打出3.5亿英镑,下面写着Let ‘s take back control。这是整个公决当中特别典型的一个场景,为了四处揽票,而突出一个虚构的事实。这里受到打击最严重的是英国的官方统计部门,比如英国统计局局长安德鲁·迪尔诺特爵士说,这种说法完全是不对的,它是在误导而且破坏了英国人对于官方数据的信任;英国财政研究所把这个数字称之为荒谬的。但脱欧派根本不理这一套,而是继续高喊口号说:我们英国人每周向欧盟送3.5亿英镑,让我们把这个钱拿回来给我们的国民健康系统,让我们投票离开欧盟。最终,他们胜利了。
我当然不是说因为这个口号就胜利了,我是讲脱欧派的传播策略如何有效,包括它所拿出的价值3.5亿英镑的虚构事实是如何有效。赢得全民公投以后,大家要清算,说脱欧派采取很不光明的手段赢得了公投。这时有一个脱欧领导人说:这是个错误;另一个脱欧领导人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望;他们轻描淡写地就把这件事打发掉了。我们看到,这就是当下政治景观的一个核心场景,通过一个数字、一个口号,去争夺你的头脑份额,去打击你的情感的柔软下腹部,最后获得非常可见的政治结果。这是2016年发生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来到大洋的另一岸,2016年特朗普出乎意料地当选为美国总统。我记得宣布大选结果的时候我正好在柏林,参加柏林的Falling Walls Conference,为了纪念柏林墙倒塌而举办的一个系列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各种各样的falling walls,比如说在女性主义这个领域应该有哪些walls需要推翻,在世界经济中有哪些walls需要推翻,也就是说,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墙“倒塌。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前一天的时候,诺奖委员会的主席正在讲话,说第二天特朗普选举的结果要出来,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自由世界的末日,因为我们都非常恐惧特朗普当选,他的当选对我们这个会来说,构成一个巨大的讽刺。因为特朗普当选的核心诉求就是要立更高的墙,跟柏林墙被推倒的信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大家都忐忑不安,欧洲的那些精英在那里开会,不知道第二天特朗普是否会获胜。第二天所有的人在会场的大屏幕电视上看到特朗普获胜,我看到当场有人痛哭。你想象不到这事对于所谓的欧洲自由派人士的打击。默克尔突然之间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因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不再是美国了,人们认为只有默克尔捍卫了欧洲原来的那些价值。
特朗普当选是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所以后来有人批评说,你们精英太脱离民众,不知道民众在想什么。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包括特朗普现在还在大选,但我们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脱离了今天讨论的场景。
我想说特朗普上台后,跟后真相的关系到底在哪里?特朗普就任以后,他的政府和盟友宣告:“总统是真相的唯一可靠来源。”我这里截的图片是美国的一个独立媒体VOX的报道,美国众议院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史密斯说:“特朗普是真相的唯一可靠来源。”史密斯是德州的众议员,他同时说:“最好从总统那里直接获得新闻,事实上这可能是获得未经污染的真相的唯一方法。”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是“推特治国”,他绕开所有的媒体和机构,直接在自己的推特上发布各种信息。所以共和党这一边说,要想获得真相,不要去信那些媒体,信特朗普本人就好了,去看他的推特。特朗普自己全面向媒体宣战,人称media war。特朗普说所有的媒体都是有偏见的,它们都是被利益所左右的,只有我,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我说的才是对的。媒体则说特朗普真正的战争并不是同媒体展开的,它们把这场战争叫做“事实之战”,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媒体之战就是事实之战,即“向事实宣战”。
所以,特朗普消除媒体合法性的手段,首先是要消除事实的合法性。正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讨论说,为什么在2016年,“后真相”变成如此不可避免的东西。但是“后真相”这件事,从来都不是因为2016年《牛津词典》定义了它、或者脱欧了、或者特朗普当选了才有的。“后真相”当然不自今日始。
我们举一个很熟悉的例子,还有什么人描写后真相比奥威尔描写得更好吗?奥威尔就是写《一九八四》那位小说家。我们说奥威尔写了《一九八四》,难道后真相是从1984年开始的吗?当然也不是!因为奥威尔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是1939年。后真相是1939年开始的吗?你还可以不断往前溯源。
“后真相”被描述为一个当代问题,但它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它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不那么引人注目。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回到奥威尔,事实上奥威尔的这本书,在特朗普当选以后,重新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大家突然意识到,特朗普的很多东西怎么跟奥威尔写得那么像。因为《一九八四》是个政治寓言,这本政治小说其实是很糟糕的小说,我们不得不说评价小说的标准和评价政治论文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本小说我觉得是很糟糕的小说,充满了图解,但作为一个政治寓言,它是一流的政治寓言。因为在《一九八四》当中,奥威尔构建一个意识形态被大规模改变的反乌托邦世界,政府宣称自己拥有真相的垄断权。政府说“2+2≠4”,你只好承认“2+2≠4”,所以他说:“政府不让你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这是奥威尔的原话。
为什么在后真相时代重温奥威尔?因为我后面会讲信息流行病,包括后真相状态里,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们质疑任何官方的真相。我们对官方给我们的真相嗤之以鼻,我们觉得那些东西都充满着阴谋,这种质疑会和其他的因素构成当代社会的后真相状态。这个状态可以用很多特征来描述,但它起码有一个特征是:玩世不恭的怀疑与幼稚的信条这两者间的奇妙的结合。这也不是我提出的,这是佛洛姆在《逃避自由》这本书里提出的。佛洛姆在1941年抨击现代文化,发现这个所谓的“玩世不恭的怀疑与幼稚的信条的奇妙结合”,导致双重的结果:
第一个:每个人对他人言论或者报章刊印的东西,都抱持怀疑主义与犬儒主义的态度。就是我们不信你,你说得越天花乱坠我们越不信你。第二个:每个人又同时幼稚地相信别人以权威立场所说的任何内容。所以佛洛姆很犀利地说:“融合了愤世嫉俗与天真轻信的心态,这是现代人的典型特征。”这是20世纪上半叶提出的真知灼见,那个时候甚至还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和移动媒体了。佛洛姆的分析对不对?他证明“后真相”当然不是由于有了社交媒体才出现的。刚才我提及奥威尔,奥威尔讲到一个强大的真理部下令你效忠一个口号:“自由即奴役”。这么一个矛盾的世界被奥威尔写得栩栩如生,他也是一个后真相的先驱者。
可以举更多的例子,比如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事件,这是在斯诺登之前美国军方最大的一起泄密案。当然我们看到知情人的揭露最后公开登上《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说道:五角大楼文件显示,约翰逊政府“不仅对公众、而且对国会系统地撒谎”。我所喜欢的政治学者阿伦特,写了一篇文章专门分析政府的谎言和五角大楼文件之间的这种关系。阿伦特说:“当掌权者如此频繁地撒谎,以至于压倒了公众了解真假的能力的时候,对真相存在的信念也会消亡。”由于这句话,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把阿伦特同归于后真相理论的先驱者。
这是一本经典著作——所有念传播学的人都要读的——李普曼的《舆论》,李普曼分析新闻与真相的关系时说:“公众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愿意’相信谁,而非谁说的是‘真相’。”这话是1922年说的,所以李普曼毫无疑问是更早的后真相理论的先驱。他在这里讲真相如何取决于你愿意相信谁,而《牛津词典》对于后真相的定义是真相取决于个人信仰,所以按照这个追溯方法,可以说“后真相”存在很长时间了。
但这么说,其实又对又不对。如果仅仅说这个东西以往一直就有,虚假信息一直就有,那又能说明什么?所以你不能够只讲“后真相”有一个很漫长的渊源,你还要证实,此时的“后真相”跟彼时的“后真相”可能还是有点不一样。这里可能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后真相赋予真相以次要的重要性,这个我前边已经强调过了。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史上出现的新东西,和传统政治有非常大的不同。传统政治不管争论什么是真相或者谁有真相,起码都把自己打扮为真相的捍卫者,也就是他至少还承认真相的重要性。但是在后真相的状态下,我们觉得真相无所谓。姑且不讨论追求真相是不是值得,我们可以说真相这个事情我们受够了,我们受够了事实。这是我为什么把后真相政治又叫做后事实政治的原因。
事实以及事实背后的真相,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讨论后真相的情况下,首先需要回顾一下有关事实的近代史。我翻译了一本书《知识的边界》(Too big to know),英文可以直译为《大到不可知》。我觉得“大到不可知”在汉语里尽管会让你震动,但可能会让人觉得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严格来说我改了一个抹煞了原文尖锐程度的标题,我把它叫做《知识的边界》。这本书是美国学者戴维·温伯格写的,正题下面的副标题很长:“在大数据时代反思知识,因为事实不再是事实,专家随处可见,而屋子里最聪明的人是屋子。”
在《知识的边界》这本书中,温伯格根据事实的基本形式的变化,把事实的近代史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叫做“经典的事实时期”(Age of Classic Facts),事实是相对稀缺的,需要付出较大的努力才能发现,并且用事实用来证明理论。当我讨论到这一点的时候,马上想到科学的先驱弗朗西斯·培根,因为没有培根就没有科学实验方法,他为了寻求普遍性的知识,主张通过一系列个别事物的实验来得到知识。所以从培根以后,整个西方的知识范式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我们不再通过逻辑推理来得出知识,事实是通过实验获得的。这个时候事实像一块块砖瓦,我们会认为理论是由事实构建的,就像房子是由砖瓦所构建的。
没有培根就没有科学革命。很多人知道培根说了一句著名的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很多人不懂培根在整个知识范式当中的重大意义,这个意义远远超出科学。比如张寅讲历史,我讲传播(传播当中很大程度是新闻),张献民或者周佳鹂可能讲影像真实……所有的人都在讲什么?我把它总体归结为:我们所有人都在讨论一个东西叫“事实文化”。也即观察或目击到的事物或行为,我们把它们叫做事实,事实可以导出真相。
事实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域,从法律到科学,从历史到新闻,所以在经典事实时期,事实大获全胜。我们意识到,没有事实的新闻不是新闻,没有事实的历史不是历史,没有事实的法学不是法学,没有事实的科学肯定不是科学。所以第一阶段事实大获全胜,而这要归根于培根这些人。
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也是大型计算机刚刚开始应用的时候,我们进入了“基于数据的事实时期”(Age of Databased Facts),事实一度占据的地位被数据所取代。这个过程既有进步,也造成很多认知混乱,因为收集和权衡事实需要调查、辨别和判断。同时,由于人类生产的数据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把越来越多地将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外包给机器,直到形成今天的大数据时代。
在大数据时代,甚至我们都不太在乎事实是什么,我们要的全是数据,我们把事实作为电子信息流上传或下载。由于数据堆积如山,最后人类又不得不发明一系列的机制,来试图使我们从信息的超载当中解放出来。
本来我们是有这么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按照过去对知识范式的变迁的研究,我们将其称为“知识守门人”。知识的守门人有很多,比如原来教师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守门人。如果你当老师,你没有一桶水,怎么给学生一碗水?如果你不能够替学生过滤知识,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老师,所以老师是知识守门人当中的一种。守门人也未见得全部都是“人”,从物的角度来说,例如百科全书、词典、教材,都是知识的守门人。
但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老师的权威瓦解了,学生不在乎你,学生也并不听你的,你说服学生也挺无力的,也就是你丧失了权威。教科书的权威瓦解了,百科全书的权威也瓦解了。我布置学生写论文的时候一定有一条规定,“凡是在论文当中引用百度百科的一律不及格”。不管你论得多好,只要你的论文里有一条引证来自百度百科,我直接判你不及格,因为我认为百度百科不是合格的知识守门人。
传统知识权威瓦解了,瓦解以后必须用什么东西填补这个真空,需要找到办法来填补它,而我们的特点是以技术应对技术。我们离开技术什么也不会,技术造成的问题我们用技术去解决,姑且不管能不能解决,反正我们用技术去解决,因此我们找到两种方法。也就是说,新的知识守门法有两类:
第一类叫算法机制。我们不信任人,我们把信任交给机器,机器替我们决定什么东西最好。机器很多地方会比你做得好,比如说中午出门跟朋友吃饭,打开百度地图,它会一路告诉我到哪该拐弯了,还有多少米等。不知道应该去哪吃饭,那么可以用大众点评,不仅替你选择餐馆,连某家餐馆里什么菜最受好评都告诉你。算法机制很好,替我们解决生活当中曾经困扰人那么多年的迷路问题。
第二类叫社交机制。我们不再信任专家,我们信任我们所熟悉的、所喜欢的或者所尊重的人所构成的网络。这个听上去也不错,前提是你有意识地建立这样的网。
然而这两类技术解决方法各有各的问题,这些问题到现在我们仍然不能解决。比如说算法机制,可能会造成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社交机制,可能会造成回声室效应、圈层传播等,它们都不是绝对完美的信息过滤方法。
但无论这个机制是否完美,人类来到现在这个地方,由此我们进入事实发展史的第三阶段:网络化事实时期(Age of Networked Facts)。如果经典事实和数据事实被看作从根本上构成孤立的知识单元,网络化事实的特点是:它是网络的一部分。而这个网络化的事实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温伯格原书的标题——它大到不可知。简单给这个说法一个解释,就是有太多的知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的。
所以我们最终来到一个什么阶段?我们看见事实被人们捡起来,摔到墙上,它们自相矛盾,分崩离析,被夸大被模仿。我们正在见证牛顿第三定律的事实版本:在网络上,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这意味着不管你提出多少知识,总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反事实,并用它来驳斥你,这就造成网络讨论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你永远不要跟一个傻缺辩论,因为傻缺会把你拉到他的水平上,然后用他的水平打败你;如果我们用比较文雅的话来讲就是,你永远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所以网络讨论是不可能的任务。
进一步展开,“大到不可知”是什么意思?大到不可知,其实对我们造成了巨大的认知影响,我把它分为三点:
第一点,可用事实的数量大增,本身就会使人们对真相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这句话很容易理解,今天你在网上读到豆腐不可以和菠菜一起吃,明天有人告诉你网上说了豆腐就要和菠菜一起吃,最后你对豆腐和菠菜是不是要一起吃这事已经不在意了,因为你搞不清楚谁对。要不要吃转基因食品?小孩生病了打不打疫苗?到底中医对不对?……网络上有一些话题永远不可触及,因为它们会让你割席。
而又因为我们可以随手获得如此多的事实,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结论的能力。我有一个比喻,互联网像一个巨大的洗牌机器。如果去商店买一副新的扑克牌,这个扑克牌的排法是有规律的:大小王之后可能是红桃A一直到红桃K,接下来方片A到方片K,因此你会知道这个世界有规律,因为下面那张牌是什么你知道。但互联网把牌全部洗了以后,方片A后面可能是草花3,草花3后面可能是黑桃5……然后你丧失了得出结论的能力,因为总是有其他事实支撑其他的看法。
第二点,网络更加强化了我们原有的立场。为什么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呢?因为我们讨论来讨论去并不是在寻求共识,我们讨论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强化自己对某个事情的认识。哪怕你给出一千条一万条反驳我的东西,我总还是认为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相信和确认他们已有意见的“事实”,并驳回跟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事实,这在心理学中叫做确认偏误。
新闻学、传播学要教的一个基本的东西,甚至作为媒介素养课在小学就应该教的东西,叫“一定要把事实和观点分开”。但今天你发现这个事情完全不可能做到,事实和观点有些像女生用的不同的化妆品,在脸上是混在一起的,根本没有办法分离出来。也就是说,事实与观点之间不再泾渭分明了。
第三,网络讨论的不可能性,导致在互联网上分歧将永远存在。因为不论何种观点,网络上都有人不赞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同意。换言之,你来到奥威尔世界会发现,“2+2=4”真不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有一大堆人告诉你“2+2=5”,他们给你提供一大堆的证据来证明二加二的确等于五,最后把你自己也弄糊涂了,觉得二加二可能就应该等于五。所以,千万不要随便跟人辩论,因为就连那些你自己最深信不疑的观点,可能也是禁不起辩论的。
总结一下,如果还有事实的存在,我们就来说有一个有关事实的事实:无论我们有多“大”的数据,多广的网络,多自由的言论,在21世纪,都无法确定人们是从信仰还是从事实知其所知。所以后真相时代百分之百会到来,我们再也不能够对任何事情加以证明。可能有同学会批评,我这样是不是走到了一个极端?也不是。如果要给一个更加准确的描述,我会这么说:“事实依旧是事实,但是它们不再充当社会基石。”
事实的重要性大幅度下降。我相信所有做纪录片的人都还坚信自己记录的是事实,我也坚信作为一个新闻学教授,我所传授的东西是事实,但问题是,我在说服其他人这些是事实的时候,要比以往费更多的力气,而且你最后也不一定认可我,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情况。
2020标语,停止信息流行病(Stop Infodemic)(取自开源库)
已故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这句话在几十年前,人人都觉得它表述得很经典:“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实。”在事实和观点泾渭分明的年代,这句话是真理。我不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事实总归是事实吧。
如果你说事实总是事实,这就意味着,我可以拿出“一个东西”摔在这里,试图终结我们之间的讨论。因为你总得承认事实,你总得承认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你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所以,事实在这里扮演一个分歧终结者的角色,但是我们今天发现,事实不再能够扮演这个角色了。你以为你捞出一个事实摔在这里,另外一个人却斩钉截铁地说你说那个不是事实,所以网络化事实开启了一个充满分歧的网络。
由于分歧将永远存在,我们就来到了后真相世界。这个世界通过一系列更多的技术在不断地增压,包括智能手机、人工智能、基因编辑,以及可能会日益发达的洗脑术、信息流行病等。现在新技术允许个人实时投射未经过滤的新闻版本,高度党派化的意见在社交媒体上也可以大肆流通,所以无视证据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阴谋论会大行其道。
阴谋论这件事情难以处理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在于,就连反对阴谋论这事,也会被阴谋论者认为是阴谋论的一部分。所以无论你怎么反对他们,阴谋论者永远是胜利者的姿态。
这就构成一个巨大的矛盾,在一个信息横流的世界里,我们反而不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已经不能够就人类如何获知(how to get knowledge)这事达成一致了,更不要说界定什么是知识(what is knowledge)了。在这样一个传统的知识守门人瓦解、新的知识守门人正在形成但仍然有巨大缺陷的时代,中国一句古老的谚语可以完全颠覆掉:“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
好的信息不见得能够战胜坏的信息,弥尔顿的言论自由市场可能也失效了。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来讨论新冠病情肆虐以来出现的新的场景,也就是我下面一个主题——信息流行病。
在新冠病毒刚刚起来还没有多久,世界卫生组织的反应一波三折,一开始觉得这不是一件大事,后来发现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在2020年2月2日的时候,世卫组织宣称说:“新的冠状病毒的爆发与反应,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信息流行病。”信息流行病这个词是一个组合词,英文是infodemic,是由information+epidemic组合而成。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信息流行病一个定义,特指信息过多,有些准确而有些不准确,这使得人们在需要时难以找到可信赖的来源和可靠的指南。世卫组织不是一个学术机构,它的定义是我们所谓的working definition,是一个工作定义,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定义已经足够了,因为它已经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流行病的基本元素。
第一个叫做信息出现大规模集聚。信息流行病的前提是有太多的信息,信息是瘀积的、超载的,而它的流行乃是在大量传播信息时,多种人类和非人类(即机器人,bot)资源同时行动的结果。其中,需要注意的是,非人类账户已成为社交媒体中噪声的重要贡献者。
第二,信息以极快的速度到处流传。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交媒体和移动设备的信息呈现方式要求人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摄取信息,另一方面,不可靠或误导性的信息也比基于事实的新闻传播得更快。当用户反复受到来自不同来源的给定信息的冲击时,等于间接验证了它们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导致用户反过来亦积极传播这些信息并成为误导性信息的载体。
第三,世卫组织的定义留有余地说,信息“有些准确而有些不准确”,我觉得世卫组织在这个地方可以直截了当地讲,其实这些信息当中大部分是不准确的,只有少部分是准确的。换言之,我们看到信息流行病当中的信息,基本上都是错误信息、伪传信息、阴谋论,甚至是赤裸裸的谎言。大家会注意到我从来不用“谣言”这个词,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读我的一篇论文《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我对谣言的讲法跟大多数流行的传播学讲法是不一样的。但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区分错误信息和伪传信息?这当然不是我做的区分,世界上很多研究信息的人都做这样的区分,这个区分在中文语境下很难讲,因为它一个叫做misinformation, 一个叫做disinformation,这两者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因为disinformation这个词更多讲的是有些人有意传播的假信息,还不简单只是错误的信息,所以我把它翻译成“伪传信息”。阴谋论就是一种特殊的伪传信息。所有信息流行病当中,流行的信息大部分是这一类信息。
第四,我们会发现信息超载和信息传播速度过快导致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你没有办法在众多信息当中找到关于某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这跟我们前面讲的东西相呼应,当某个事情被“洗牌机”洗了以后,我们不知道下一张牌是什么,因此获得信息和采取行动之间的纽带被一刀切断,你陷入无所适从。信息流行病其实最终要达到一个结果:让你行动上完全陷入麻痹状态,让你没有办法行动。
所以我们用这些来解释什么叫信息流行病。为了给这个东西做注脚,2020年9月22日,世卫组织联合多个国际组织发表声明说:“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第一场大流行,在其中人们大规模使用技术和社交媒体来保持安全、知情、生产和联系。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赖以保持联系和知情的技术正在启动和扩大一种信息流行病,持续破坏全球应对措施,并危及控制大流行的措施。”
为什么从2020年2月到9月,世卫组织一直不断地在大张旗鼓地说这个事情?因为信息流行病愈演愈烈,一方面有大量的错误信息,另一方面有大量的伪传信息,这两者各有各的目标。错误信息在流行病中一定会导致生命的损失。比如郑州的一位老兄相信某种中药能够医治新冠病毒,他出门去买这个药的时候患上了新冠病毒,这就是一条错误信息所造成的现实结果。伪传信息主要打击的目标是公共辩论,其目的是扩大仇恨言论,增加冲突和暴力,最终威胁到有关民主、有关人权、有关社会凝聚力的一切东西。错误信息和伪传信息各有各的作用目标。
作为一个国际机构而不是一个政治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应对冠状病毒,如果不同时对信息流行病进行进行某种程度的联合遏制,我们就不能够完全地处理疫情。这是全世界的共识,必须解决信息流行病。在《柳叶刀》这样的专业杂志上,那些专家们都出来呼吁,必须遏制这个所谓的infodemic。突然之间这些科学家发现,如果我们不在社会科学上对信息流行病进行辨别,它会直接影响科学这方面的措施。有句谚语说:“历史总是会重演”。其实历史不大会重演,但是我相信历史有时候会非常押韵,比如说信息流行病这个词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发明的,这个词的前身在SARS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网传阿波罗号登月计划(Apollo Program)阴谋论
和“后真相”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的原始出处。美国一个智库的CEO大卫·罗斯科夫(David J. Rothkopf)2003年在《华盛顿邮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When the Buzz Bites Back》,在这篇文章里,Rothkopf说得很清楚:“SARS的故事不是一种流行病,而是两种,第二种流行病基本不为媒体所
注意,但是它的的影响却远远大于疾病本身。这是因为造成SARS从一个糟糕的中国区域性健康危机转变为一场全球经济和社会溃变的,不是病毒传染病,而是信息流行病,即infodemic。”这是Rothkopf第一次提出这个词,他给了一个定义:“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现实完全不相称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他接着讲道:“信息流行病正在成为人类已知的最致命现象之一,能够立即穿越大陆。几乎在所有方面,其表现都与其他疾病一样,具有流行病学所固有的可识别的症状,有知名的携带者,甚至可以直接治愈。迄今为止,许多当权者似乎无法遏制它们或者不愿承认它们的存在……这些由互联网或媒体传播的病毒会造成全球恐慌,引发不合理行为,模糊我们对重要潜在问题的看法,使我们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打击市场并破坏政府。”
这是Rothkopf的完整论述,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原封不动地挪过来,挪到今天来描述新冠疫情。最终无论我们讨论SARS还是讨论冠状病毒,所谓信息流行病的出现,本质上都是在传递事实、谣言、解释和宣传方面的某种组合。大家注意我刚才把信息流行病中的信息分成四类:错误信息、伪传信息、阴谋论和谎言。我把谎言放到最后,为什么?因为谎言这个事情越来越技术含量偏低,最好的东西是把谎言和事实掺起来说,这是最有效的策略。所谓disinformation所干的事就是这样,它也不是全然说谎,有些东西说得挺对的,但它显然在一些重要的地方说得是极其不对的,然后把这样的混合物打扮成对传递给你。所以我说信息流行病传递的是事实、谣言、解释和宣传的某种组合。“事实”在这里只是扮演着传递其他东西的功能与角色,“事实”被用作一种原料,这是非常崭新的东西。
当然Rothkopf也讨论到,这里面要分析媒介的作用。我很惭愧地讲,传播学其实在整个社会科学当中发展得不怎么样。这个学科它本身的影响力,它的产出其实都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张献民老师不看传播学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我同时要说,这不等于“传播现象”这个事你不需要注意,因为其实所有的事情都绕不开传播,只是说传播学者在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有所失职,他们做得不够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此,当你看到信息流行病的时候,一定要去发现这个东西同媒介的关系是什么。信息流行病是一个复杂现象,主要通过媒体来作用。Rothkopf说:它是一种主流媒体、专业媒体和互联网站以及非正式媒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发的复杂现象。Rothkopf写这段话的时候是在2003年,那时还没有社交媒体,大概最接近于社交媒体的东西叫做短信。因为我本人是SARS的亲历者,在北京,很多的消息是通过短信流通的,所以短信在这里就是非正式媒体,所以信息流行病是一个正式媒体同非正式媒体之间的一个复杂现象。但不论正式媒体还是非正式媒体,最终传递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上边我所说的“传递事实、谣言、解释和宣传的某种组合”。
SARS跟我们今天的新冠病毒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来说:新冠病毒是历史上第一场社交媒体信息流行病。在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关于新疾病的信息,能够比2020年的冠状病毒流行,在一个互联世界中传播得更快。死亡人数和细节通过24×7的滚动报告实时通达全球,数十亿手机用户不断访问新闻,数以亿计的社交媒体来源,构建了永不止歇的对话场。这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东西,尤其考虑到社交隔离,有多少人在家里仅仅凭着社交媒体与外界沟通,从社交媒体上获取信息?随着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封锁,用于传播信息和开展交往的社交媒体基础设施,正在达到前所未有的新规模。这是Rothkopf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不能够想象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又是一致的,就是假新闻和伪科学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是一个大杂烩。它是掺杂在一起的,只不过它的范围、广度、深度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把这个现象叫做全球首次大规模信息恐慌。之前有过寨卡病毒,有过SARS,有过中东呼吸综合症,但是新冠大流行发生在人类拥有密切的相互联系以及身处应接不暇的信息洪流这样一个前提下,所以出现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第一场大规模的信息流行病。
为了说明今天的信息流行病与Rothkopf时代有何不一样,我们就不得不讨论社交媒体的交流特性,因为Rothkopf没有触及社交媒体。现在,你天天用社交媒体,有没有想过社交媒体有一些很根本的属性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社交媒体具有两大特性:第一个特性是个人因素,凡是社交媒体的消费者都是个体。以往大众媒体的消费者不见得是个体,但社交媒体的消费者一定是个体。因为社交媒体的交流发生在有个人关系的人或者是互相欣赏、互相尊重、互相认识的人之间,因此交流在社交媒体上不是一个无名的、面目不清的行为,也不是大众媒介的推送,交流者是你的父母、邻居、朋友、同学、同乡等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一切亲近的人。相信和人自身相近的人,是人类的天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展出一种算法叫社交过滤。我可以不信任央视让我购买某一个东西的广告,但是如果我姐姐说那个东西挺好用的,我第二天就下单了,因为我信任她。这其实是我们人类进化过程当中一种生存的本能,我们会相信跟我们相近的人,同时利用网络节点加上链路这样一个基本的网络结构,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具有潜在的到达全球受众的潜力。虽然它是个体的,但是它的确又可以大范围传播。这是《信息时代三部曲》的作者卡斯特提出的一个现象,他说这叫大规模自传播。听上去这词很矛盾,但同时存在,既可以大规模,但同时是自传播,可以凭借传统媒介渠道难以实现的方式扩散信息。
第二个社交媒体的特性,我把它叫做“级数效应”。级数效应即一个信息可以在社交媒体上重复曝光,可以像病毒一样人传人,这就进入到病毒式传播了。你会突然发现,我怎么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多耸人听闻的新闻,动不动哪个地方就会发生一个让人完全无法索解的社会新闻。以前我怎么不知道这种事?其实以前也有,以前你可以在小报上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和耸人听闻的说法。但是今天为什么你觉得这种事情听到的越来越多?因为同样煽情的标题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出现,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所有这些东西会反复冲击你的眼球。它会通过各种方法,比如通过分享、评论、热搜,通过被社交媒体算法置于你的信息流顶端,最后让你无所逃避,所以这类社会新闻你想不知道也不可能。这让我想起麦克卢汉所讲的“部落之鼓”,“部落之鼓”的意思是说在部落时代有人一敲鼓,全部落的人都听到了。你说我不想听到,比如我本人不关心鹿晗,可是所有人都告诉我鹿晗有女朋友了,鹿晗有女朋友跟我有什么关系,完全没有关系,但是鹿晗有女朋友这事一定会传到你的耳朵里,因为“部落之鼓”敲响了。这就是级数效应。
我们会发现,讨论错误信息或伪传信息的时候,级数效应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点,就是反复暴露于某一虚假信息,一定会增加这个信息的可信度。三人成虎,第一遍有人说你不信,第二个人又说,第三个,连你最亲近的姑姑也这么说了,你就觉得这件事可能是真的,这叫“真相幻觉效应”。我们人是一种错误百出的动物,其实人处理真相的时候跟一个傻瓜一样,因为我们评估“什么是真相”不是依据某一个客观的标准,而是有五花八门的认识方法。有一种方法是:如果某一信息我特别熟悉,我就倾向于认为它是真的,因为我会把新信息跟自己以前已知的旧信息进行比较,凡是那些突然冒出来、跟我以往的信息不具备相似性的东西,我本能地会觉得那个信息不对,是错的。重复会使一个陈述易于处理,结论显得更加真实,这是社会科学研究证明了的。“真相幻觉效应”是被许多实验证明的,熟悉可以压倒理性。如果被反复告知某个事实是错误的或者某个事实是正确的,最终就会影响听众的信念。
今天有一位老师在讲阿姆斯特朗传记电影,大家知道有相当多的人认为登月完全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骗局吗?很多人认为登月是假的,包括阿姆斯特朗插美国国旗,“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等,都是美国政府伪造的,为的是在冷战中向苏联人示威。如果同意阴谋论的说法,阿姆斯特朗就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英雄,而是最大的骗子。登月阴谋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流传,但这个荒谬的说法,在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继续传播之后,很多人认为这一说法得到证实,而不再感觉自己属于少数派。
“谎言重复多次,就会成为真理”,如果看看周遭,你可能开始感觉从广告商到政客都在利用这个人类心理的弱点。而包含虚假信息的社交媒体帖子有一个特点,即它会巧妙激发人们的分享,反过来这又进一步扩大了级数效应。所以,后真相在社交媒体时代大行其道并非偶然,或者按照我刚才所说,后真相出现很久了,但是它变成我们不得不应对的一种基本状态,必然是在有社交媒体这样一个基本技术前提下,才可能成为现实。
基斯·哈林(Keith Haring), 《无题》(Untitled),1983
一个行为者,当她行走这个世界的时候首先要获取信息,不能获取信息就没办法决策,因而就要面对一个信息生态系统。当她难以决策的时候,过往依靠什么东西?她很可能会依靠神谕,如占星师、占卜师、巫师告诉她怎么做她就怎么做,因为她信息不够,自己决策不了。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我有一个学生是泉州人,泉州的关公庙香火极其旺盛,据说非常灵验。当地有很多人拿着“筊杯”,是一种占卜工具,在庙里往地下摔,看落在地下的时候,是一阳一阴还是两阴面,然后决定自己应该选择是或否,其实对于计算机来讲就是1和0的选择。但泉州的这个东西特别神妙,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两阳面,表示神明也没有答案。有时候老师要处理学生的一些困惑,比如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学生来问老师该怎么决策,遇到这种问题我基本上回答不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位泉州的同学就回到家乡,要去求关公。但关公给她的答复就是第三种,最后的结果,就是她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在信息不充沛情况下,如果你有水晶球,你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你就很容易选择,但是你不知道,信息不对称,因此你就选择不了。
面对今日的信息生态系统,会发现三个主要的相互关联的元素,我们是围绕这三个元素展开行动的。
第一个元素是社交媒体本身,我们把它称之为平台;第二个元素是讯息,就是通过所有信息传递的内容;第三个元素是这些内容的消费者,即受众。社交媒体的这三个元素,前两个——平台和讯息——是相互增强的,这是社交媒体的技术特性所决定的。平台本身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信息能够快速地分发给所有信息的消费者,并且这个东西越具有病毒性,平台的算法会越把它推到最前面,因此它优先传递可以带来流量并由此产生收益的病毒内容。这和平台的利益密切相关,所有的平台都是这么设计的。它考虑的不是受众的利益,考虑的是自身怎么拥有最大的眼球,眼球怎么转化为广告,关心的是转化率问题。因此平台的这个特点,导致它天生就容易受到旨在煽动的虚假信息的影响,换言之,凡是那些煽动性地捕捉你的情感的虚假信息在平台上永远拥有优先权。我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活动,我也发言,我也写公众号,可是我的话没人听,因为平台不会把我的东西放在优先位置上,即使假定说我跟哪个平台关系好,这个平台今天把胡老师的东西推出去,结果也会是没人看,因为我的东西标题不够吸引眼球,内容不够耸人听闻,太理性了,看上去很费脑筋。所以在平台上大行其道的东西,一定是我前面所说的那些东西,这些信息仿佛病毒,本身就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将自身最大限度地予以分享。病毒的特点就是不断地复制自己,找到一个一个的宿主,寄生在他们身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平台和讯息这两方都是高度可疑的。
照这样说,我们岂不是都进入了死胡同?并没有。其实不管平台和讯息怎么样,在这个信息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元素始终是受众,也就是始终是你、我、他,是我们自己。虽然虚假信息的生产及传播能力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如果这些虚假信息不是有效利用人性的基本偏见,其实是不可能获得大规模传播的。虚假信息可能做到的事情是,通过算法把自己往前推,动用社交媒体机器人、水军、僵尸粉等所有这些东西来加大传播,但如果它不是精确地预测到“人并非信息的理性消费者”这样一个弱点,它也传播不开。换言之,你被攻陷的唯一原因是,你总是寻求对复杂事物的简单答案,你也总是寻求迅速而令人安心的答案,你总是企图获得某种确定感、认同感、归属感。你所有的这些美好的想象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全部都会被精妙地利用,这就是“认知闭合”。
2010-2020互联网模因(Internet Memes)合集
什么叫认知闭合?我们个体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不是特别相信泉州的关公,但我们又必须要做出决定的时候,怎么办?这时,你需要为问题找到一个明确答案的愿望极其强烈,不管这个答案有多么不完备,但是它总比不确定和混乱要好。人的特点是,在你企图做出新的决定的一刹那,你其实是拒绝接受新信息的。如果这时候你的新信息之门还是打开的,你就再也没有办法决策,在决策那一刹那你需要对自己进行一个认知闭合。在闭合情况下,你会迅速地做出决策,这个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黑白两色的世界。其实可能有很多选择,但对于你来讲,你可能只有非死即生的选择,这跟《黑客帝国》里的桥段相似,要么吃下蓝色的药丸,要么吃下红色的药丸,没有第三种选择。
在这个时候,人和人的差别就出来了。有的人对于闭合的需求比较低,换言之,她避免闭合的需求比较高,此时这个人可以容忍模糊性,但通常我们会说她是优柔寡断的,缺乏决断性。相反,另外一个人会迅速做出决策,她对闭合的需求就会非常高。每个人都不一样。认知闭合是一个连续光谱,每个人处在不同的位置上。但我们在这里加一个变量,把恐惧、焦虑放到这里面。比如说在新冠疫情特别肆虐的时候,这时你的焦虑被无限放大,恐惧也被无限放大,所有人的闭合需求全部增加。增加的意思就是,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提出有决断力的和简单快速的解决方法,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是好汉,那我们听他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强人领袖越来越吃香,因为强人领袖的特点就是这样,不管是什么东西,让我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让我们把这事做了,让我们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一剑把戈耳狄俄斯之结斩断,我们不再去试图慢慢解开那一团乱麻,这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产生认知闭合。我们会欢呼平常我们所不能够容忍的一些行为,因为它解决了你的闭合需求。
当我们把平台、讯息和受众结合在一起,我们会看到这是互联网上特别值得研究的东西,也有一个专用术语——互联网模因(Internet meme)。模因,这个词有很多种翻译,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台湾人的翻译,叫做瀰因(必须是繁体字的瀰)。这是理查德·道金斯在1976年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里首创的一个词。道金斯发现文化当中也会有一些行为,一些风格,一些要素,一些观念,特别像人与人之间的跨越散播,会有一些观念胜出,另一些观念失败。这个词后来被互联网完美地借用,特指在社交媒体上散播的模因。当然,汉语是一种特别让人容易望望文生义的语言,因为是象形字。你看到“模因”这个翻译,会觉得模因可能就是为了复制、为了模仿,但是关于互联网模因,这点是不对的。互联网模因从来不试图追求复制的准确性。它是copy,但是不是一个perfect copy完全不重要。互联网模因的特点恰恰是在传播过程中,对原有的模因进行各种各样的修改,甚至可以把它改造得面目全非,不管怎么样,如果最后的结果能够大获全胜,就OK了。
在《自私的基因》最后一章,讨论用模因来表达文化当中的各种复制的时候,道金斯使用了“病毒式的”的隐喻。所以互联网模因与疾病的流行共享一个形容词,这绝对不是巧合。因为爆发需要三样东西:首先是传染性足够的病原体。这个病原体必须真的具有传染病,我们炮制出一个模因,这个模因如果不具备流行的基本的基因,我们就不讨论它了,因此病原体的传染性要足够;第二是不同人群之间要有大量的互动。这些人必须蹿来蹿去,病原体才能有机会找到更多的宿主。在大量互动以后就会产生足够多的易感人群,即到达了临界量(critical mass),这是第三样东西。有时候流行学家都分析不清楚,为什么一个东西就流行了呢?它是在某一个门槛上突然跃过那个临界量,突然就从小众的流行变成一个大众的流行,人人皆知,人人皆用,就像《小苹果》的旋律一样在你脑中不断地回荡。由此来看,任何形式的流行,都是一个社会过程。
在社交媒体上,有三个因素会影响到我们所得到的内容:第一点,我们的一位联系人是否分享了某一个链接;第二点,该内容是否出现在你的信息流(feed)中;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否点击了它。它也可以出现在你的信息流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分享,你就是不去点击它,只要你点击它了,这个时候传播就开始了。所有这些链接和出现在信息流中的内容,它们唯一所做是事情就是呼唤你,“点击我吧”。通过什么方式呼唤你?当然是标题党,当然是那种把所有情感的词汇放在里面,把让你切身安全受到威胁的词汇放在里面,然后你就情不自禁地点击它,点击完了以后还要转,“不转不是中国人”。你一定要转,首先要把它转给我的亲人,这个事情这么重要,我的亲人要不知道怎么办呢?
所有的社交媒体公司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制造流行的传播者都精通此道,我认为他们本质上都是流行病学家。这些人竭力把流行病学知识应用于病毒式营销以及无休止的注意力吸引上,为了达到社交媒体的级数效应。所以在这里面可以充分看到社交媒体的阴暗面,它完全可以被用来进行大规模操纵。人类自从走出洞穴以后,我们就发明了无数种操纵他人的手段,但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把这些操纵他人的手段,进行翻新、升级、扩充,并且数据化和算法化:最后,我们这些企图通过数据交换方便和便宜的消费者,最后被数据所操纵。
主持人(张献民):我认为我们正在形成知识的第二种系统,我们逐渐正在找到把它稳固下来的办法。这个意思是,我是“建制派”,我会认为我们会找到一种方式来固化我们的知识,在这种信息的洪流当中形成一种稳固,我认为这个东西正在逐渐形成。胡老师关于谣言或者谎言的根本区分,还有很多其他讲述,对我非常有启发。胡老师先对我们某一种宏观的基本状态进行阐述,但他是很快从宏观状态中能够迅速到达个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同的传播学派或者是传播学者的共同特点,我得到很多教益。学艺术的学生,不一定是大众传媒方式的,更有点像“点对点”,都想“套取”一个收藏家。做电影的则是要“套取”众人。另外还有一个感触,从我了解的一些基础理论角度来说,胡老师描绘的这个平台、聚集信息等等的方式,我听起来觉得特别像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描绘的资本,就是资本进入一个生产过程的时候,它的那种盲目以及巨大的席卷,把所有东西都卷进去,当时马克思主义用的词叫“异化”,类似于胡老师现在讲的“信息流行病”。
观众1:您刚刚提到现在新的“守门人”正在形成,在您看来在后真相时代,或者面临病毒式传播这些现象的时候,新的“守门人”他所对应的群体和原来相比是否有发生变化?对于这样的群体您觉得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素养?
胡泳:这其实是另外一个话题,我自己也花很多时间研究知识的生成问题,尤其关注在巨变时代知识体系的转化问题。我专门有讲过知识的繁荣与危机,刚才部分触及是知识危机这一部分,没有讲知识繁荣那一部分。网络化知识时代的到来,对于人类还是正面的东西大于负面的东西。我可以举一些很切实的例子,这些例子既包括信息获取手段的变化,也包括这种代际的变化。
比如说我作为老师,我生活的那个年代获取知识的方式和今天的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这两者之间有天差地别的变化。因为所有的信息在网上唾手可得,你甚至都不用转身去你的书架上拿书,就是在手机上点击网页,在电脑上划拉,你就可以获得全世界范围内你所想要的各种知识。哪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是人类的进步呢?我觉得单凭这一点就可以礼赞,知识当然不是危机,知识是极大的繁荣。
但是我想讲的是繁荣背后当然有它的问题,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知识的停止点系统消失了。对于我的学生来讲,他从来不认为百度百科不能引用,他跟我争论:凭什么你认为大英百科可以引用,百度百科就不可以引用?因为这一代人,对他来讲,没有所谓的知识停止点。我们所说的知识停止点,本质上背后是知识的权威,我们认可大英百科全书编辑者的权威。但对于学生来讲他不认可,他觉得凭什么那个东西就是权威,为什么我引用百度百科写的这个东西,老师你就不认可,你是不是沉浸在一种旧的传统当中?然后他跟你争论,我当然可以说他这是不值一驳的,但问题在于,我还不能简单说他不值一驳,我还得试图驳他。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驳了他他还不心服口服。所以知识的繁荣会带来其他的问题。其实时间的关系,有些内容我没有讲完,跟这个同学提出的问题相关。
后真相状态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专业人员的死亡。专业人员不是真的死亡了,是被认为“死亡”了。这个“被认为”其实很简单,我们今天叫专家,都是在“专”旁边加一个石字旁,你是“砖家”,所以我们对你不屑一顾,所以专业人员”死亡“了。现在社会的整个建构,从机器操作到医疗,由于分工而存在,因此我们知道,尊重他人的专业知识,其实本质上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内在要求。为什么是内在要求?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不是熟人社会,尽管互联网让我们重新回到熟人社会,但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所以你一定要信任专家。如果不信任专家,怎么能在陌生人生活的社会当中获得信任呢?只有我们相信他人的知识技能和异同,一个社会才能够正常运转。你坐飞机你就得相信飞机的驾驶员。你不相信又怎么样,可以选择不坐飞机而是坐高铁,那你就得信任高铁的驾驶员,得信任高铁整个铁路的建设者,因为你的生活当中全是技术和专业。
但是伴随着人人都有“麦克风”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对于专家和专长的怀疑已经大规模污染了我们的知识生态。我当然觉得很悲哀,因为我们是搞知识生态的,但是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就这么发展。我们北大的历史老师厉害吧,名师,全国一流,他们写的东西绝对卖不过当年明月。你说当年明月写的东西不对、不好,但当年明月的影响就是比你大,那你怎么办?你当然还是可以坚持你的东西,问题是说外部的世界就是如此变化的。所以戴维·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当中有一段很悲惨的描述:“网络钟爱狂热的、偶像导向的业余者,让专业人士丢掉了饭碗。网络代表了粗鄙者的崛起,剽窃者的胜利,文化的终结,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主人是那些满目呆滞的习惯性的自慰者,在他们眼里,多数人同意的即是真理,各种观点的大杂烩即是智慧,人们最乐于相信的即是知识。”
我又引用了一个关于知识悲观的看法,其实戴维·温伯格这本《知识的边界》核心主体是对知识进行礼赞的。因为我本次讲“后真相”会主要讲悲观的这一面,但是关于其他的论述,你可以去看他的书,和我的其他文章。但我想指出来,有一个很关键的分野。
我们可以承认专业人士在很多地方丧失了专业性,甚至专业人士的操守也是有问题的,也得承认这一点。他们也可能被各种利益所左右,或者是说他们自己的专业能力太差,差到不足以称之为专家。我承认这一点,但是我想指出来,对专家的话持某种程度的怀疑是一回事,但是相信所有的专门知识都死亡了是另外一回事,这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别。如果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老师与学生、有知者和好奇的人之间的任何分野都被抹杀,即对在某个领域有成就的人和乏善可陈的人作无差别对待,那么,网络看似提供了获取知识的捷径,其实仅仅是加速了专家与外行之间的交流崩溃而已。这是我的观点。
观众2:现如今这样一个传播时代,技术导致部落化,包括形成一种情感驱动型社会。其实就包括这次疫情,大家都是闭门不出,都处在一种信息flow的状态,处在一种幽闭隔离的状态,不同的媒介形态好比说现在的短视频等,不断加剧了大家的认知闭合。但是如果放之长远来讲,疫情只是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节点,其实未来社会整个都像是一种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之下,人们的情绪也在不断影响社会的发展,那么媒介形态将来会有怎样一种发展?或者说我们虽然不能预测未来的媒介形态,但未来短视频会发展成什么,再比如,电影未来会发展成什么?以及未来的媒介形态发展和进步,会有一种怎样的准则存在?
胡泳: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首先我不是一个未来学家,很多东西也预测不清楚;其次媒介形态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最近在公号上了写了篇文章《所到之处皆媒介》,核心是讨论5G可能给媒介造成的很多变化。如果你对这个事情有兴趣可以读一下,相对来讲,我把我认为可能媒介会产生的一些变化都写到了。比如说VR和AR是不是有可能给我们造成一种新的体验;包括新闻被这种混合现实的改写;包括硬件设备,例如可穿戴设备大概会给我们造成一个新的生态传播环境;包括互联网,现在的互联网基本上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
我所说的中间阶段,是指最开始互联网是一个典型的文本事件,万维网的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把整个的Web 2.0定义为读写网(Read and Write Web),既可以读又可以写,既可以浏览又可以上载,上载是Web 2.0的核心问题。读写网的意思,就是它是以文本为主的。而现在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互联网正在从文本互联网变成视频互联网,这个趋势非常明显。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读书》约我写稿,说能不能预测关于媒体的一些未来发展,他们可能传统上对这个话题触及不多。所以我为《读书》写过关于电子游戏、报纸、阅读的未来等。我当时提到阅读的未来最终一定是阅读移动的视频。这大概是好几年前了,但今天这个场景已经完全实现了。
最简单地,你看新一代的网民在什么应用上耗费他最多的时间,以及什么东西构成他获取信息最基本的通道,非常明显目前在中国是短视频。短视频到了什么程度?比如说你为什么还要用百度搜索,百度搜索已经彻底过时了。如果我想搜索很多关于人或事的东西,我会去搜索微信;如果我想对知识进行搜索,我当然搜知乎;如果我想了解生活常识,毫无疑问我登录抖音进行搜索,抖音里面的东西应有尽有,都是视频,可以让你5分钟内变成红焖大虾的出色厨师。
视频互联网趋势非常明显。但是我预测,接下来我们将经历的一定是触觉互联网,可以在互联网上实现触觉传递,当然必须通过人工智能、VR和AR等所有这些技术。麦克卢汉最痛心疾首的是部落人本来是听觉人,被西方的字母文化搞成了视觉人,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过程,部落瓦解了。现在我们终于重新回到部落了。对麦克卢汉来讲,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人要获得自己感官的平衡,五种感觉都得用,只要有一个不用就废了,自我延伸就等于自我截除。
互联网现在大量的环境是听觉环境,也是一个标准的口传环境,互联网上流传最广的都是口传环境的东西,八卦、鸡汤、谣言、段子等等。而接下来一定会进入到触觉环境。以往最痛苦的是两地分居的恋人,叫做触不到的恋人,突然之间有一天你发现可以触到了,有可能就是媒介的下一步。这是我个人的猜想。
主持人(张献民):到时候还会是病毒式的吗?这个触觉的?
胡泳:触觉的互联网,有可能是这样,以往我们仅仅传递生活的片断,等到那个时候,可以把你的整个生活都搬上去,甚至可以在虚拟空间里重演,就是第二人生一类的感觉。这个其实也不是我臆想的,比如扎克伯格致力于要干的事就是这个事,否则他不会花钱去购买Oculus。大家有没有见过扎克伯格一张著名的照片,在西班牙巴塞罗那Mobile World Congress大会上,满屋子的人都戴着Oculus的头盔,只有扎克伯格昂首挺胸大踏步走在过道上,什么也没戴。我觉得这个照片特别绝,就像一个皇帝君临他的臣民,所有的臣民都沉浸在扎克伯格所酝酿的那个世界里,只有扎克伯格是高出于所有人之上的,所以触觉互联网也有它的问题。

观众3: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第一个您讲到后真相时代,面对后真相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有些新闻媒体如果传播一些错误的新闻,国家对这方面进行管制;再者,我们新闻从业者要提高自己的自身能力,提高自己对于新闻的辨别认知能力。我不太清楚,如果以受众的身份来看,尤其新闻出来,开始舆论朝一个方向走,后来又全部反转,作为受众在后真相环境中该怎么去做?
第二个问题,字节跳动旗下有两个产品:一个抖音,一个今日头条,我觉得这两个产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是根据大数据、算法不停给我推送。我今天划着看一个东西,它给我推送的剩下全部都是与这个相关的东西。久而久之,我喜欢看这个观点,它给我推的也是与之相关的观点,我觉得时间长了就会给我造成一个信息茧房。按道理,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应该是更加开放和多元,但是在它造成的信息茧房下,长期看同一个相关的东西,就以我个人而言,会觉得思想慢慢变得狭隘了,得不到对一些问题更多方面的想法,反而更加偏激了。甚至有时候跟网友讨论一个问题,会发现网上又很多杠精,就是对一个问题很激进或偏激。您觉得这与现在的大数据、算法是否相关?
胡泳:你刚才最后说的这点,这个显然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研究了,关于算法所造成的结果,我觉得你的观察显然已经被很多研究证明了,这个不用再多讨论。一定存在这个东西,而且所谓“算法没有价值观”是错误的,我的确认为算法不是中立的,算法是有伦理的,不重视算法伦理,就会产生大量问题。
回到你前面说的第一个关于媒介素养的问题,可以把它分成两个东西来看。第一个东西,我把那些有志于以新闻或者传播为职业的人分成一类人。因为你是从事这个的,你就应该拥有某种我称之为“记者的思考方式”,这是我的一个说法。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觉得新闻传播学院学的东西不行,不行不是因为新闻传播不行,是因为传授的人以及传授的内容有问题。我们都会承认,如果你是一个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你可能就拥有法律思维;或者你是一个工程学院毕业的学生,你拥有工程思维。其实我觉得记者本身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有关如何求证、如何辨别信息质量的高低的一个专门学问。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开发并且传授的,至于它现在没有人做,是另外一个问题,牵扯到整个新闻传播学院的教育改革问题。
我还有另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很多人也不以为然,因为我跟传统的新闻教育理念背道而驰,我觉得新闻教育最核心的东西是教授新闻理想的破灭,而不是教授新闻理想。因为教授新闻理想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学生一进入社会,进入到媒体,他马上发现教科书跟他讲的完全不一样,他就丧失了信心,觉得被骗了。我们的新闻传播学一向教那些“原型”英雄,比如说在水门事件中记者多么了不起,应该像那样的记者一样。其实你应该教的是新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是多么的艰难,要想走这个路的人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克服多大的障碍才敢于去走这个路。经过这样的一种传授,凡是应该留下来的就会留下来,凡是不留下来的就无所谓,而不是给他一个虚幻的理想。推而广之,我个人觉得教育的最高目的就是传授各种理想的破灭,而不是传授理想本身。当然我这个观点可能偏激,这是很多人不同意我的原因。
第二,如果不讨论以传播为职业的人,只讨论普通人,普通人(即受众)的媒介素养,这里我有另外一种观点。新闻传播学院在所有大学里都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因为其他学科的人觉得说这个学科哪有学,你就是实践。如果以前学新闻你就练写作、摄影、摄像,现在你就玩新媒体运营,这一套套东西全是干活,哪有学问?其他社会科学觉得新闻传播不是学问。业界也不认可你,业界说学生到我们这里来以后基本的东西都不会,我们还得告诉他怎么干活,他们只弄了一肚子的概念,什么都不会。新闻传播学院有这样一个巨大的问题,因此很多人分析这个问题哪里来的?然后这些人又提出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新闻学院的学生没有人文素养,要搞通识教育、搞素质教育、搞博雅教育,教给他们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能用到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教给他们。

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是反的,什么叫反的?如果你能够造就一个可以培养新闻思维的学科的所有必备条件,也就是做出一个响当当的新闻传播学科,不是其他学科来教我,是我反过来,为大学的其他学科开设媒介素养的通识教育。也就是说,我要让所有不是做传播的人,懂得传播这个事不是你想象得那么简单,不是所有人都能玩好的,这里有大量的东西你不懂,而你不懂的,会对你造成致命伤害。这是我们要开展的事业,我们要把新闻传播变成人文教育、博雅教育的重要部分。当然我的这个理想太高远了,以至于我总是很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