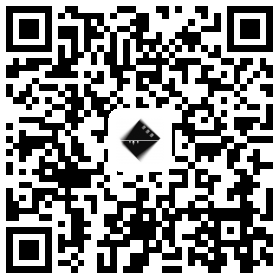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 The 4th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简称“IDF2020”)(简称“IDF2020”)是集纪录片推优、提案、展播、论坛于一体的高品质人文艺术平台。本届年度主题为“生·活”,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
IDF学术 · 论坛:
正式开幕,开启为期四天的思想激荡
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学术论坛(IDForum)动态主视觉
2020年10月16日下午,浙江省广播电视局与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学术论坛正式开幕。开幕仪式由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学院副院长刘智海致开幕辞,IDF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副教授周佳鹂担任学术主持。IDF学术论坛聚集了诸多专家学者,同时也吸引了广大的观众热情参与。
IDF学术(IDForum)是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的学术版块,旨在以宽阔的视野、深度的思考,整合与更新纪录片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以此来伴随和支持纪录片创作中的艺术探索与社会实践。本届论坛学术主题为“后真相时代的影像真实”(Reality of Image in the Post-Truth Era),由学术讲座、学者论坛和作者论坛三部分构成。

论坛开幕致辞:
刘副院长在致辞中感谢了各位学者、嘉宾及观众莅临金秋的中国美术学院,并期待大家敞开心扉,共同真诚、自由地探究大家今天所关注的纪录片的话题、纪录片的语言、纪录片的学术,为纪录片的学术发展奉献力量。最后对IDF论坛的顺利举办表达了美好的祝愿。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学院副院长刘智海
第一场学术讲座 :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姜宇辉,为大家带来了IDF论坛的第一场学术讲座,主题为:假若媒介永生——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着一种“生态电影”。姜宇辉教授以生动的语言,深度的思考,互动式交流,呈现了IDF论坛的学术高度与深度,同时正式开启了IDF论坛为期四天的思想激荡。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姜宇辉
IDF论坛的第一场讲座,紧扣“后真相时代的影像真实”这一大主题,不仅进行了媒介的探讨,还有对艺术的思考,同时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新思想进行呼应关联。从人跟数字媒介、数字天国之间的博弈,浮士德式的交易作为一个引子,引出媒介在人类历史上的三种维度:框架、流动、聚合。再由此引出对于影像的思考,即“生态电影(Ecocinema)”这个专有名词在“物“与”观“之间的探索,从而最终引导我们思考怎样在当今这个时代去思考“生”、“人类存在”等概念。疫情之中,每个人都应该思考一下,万物自然与人生死之间的关系。
“怎样从物这个角度,从媒介的聚合里跳出来,首先我们应该区分环保电影与生态电影。无论从制作手法还是创作理念,以及背后对待媒介的基本态度,对待世界的态度,两者是非常不一样的。生态电影(Ecocinema),强调回归媒介的能量流这个物质基础,将重心置于唤醒意识和激发行动。”

姜宇辉教授通过探讨“物导向”的本体论、媒介之可朽与不朽、“观”与“物”等学术问题,对“生态电影”进行了精彩地解析,并指出Maricondi式的“生态电影”缺陷。进一步对Bozak“碳平衡(carbon-neutral)”电影、“无光影像(sunless image)”、“无电影之电影(film without film)”等观点进行了学术探讨。
“不要用永生的东西,麻醉我们今天的生命,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可朽的。不要用媒介的东西,麻痹我们自己有一个数码的天堂。我更强调回到人本身的体验,不仅仅谈论物的衰亡和世界的客观,生态电影对大家的启示也在这里。在人类的真相中有更大的真相。”
姜宇辉教授的总结,激荡了会场所有人的思想,一场基于学术的观众互动交流由此拉开序幕。现场观众积极互动,很多人向主讲人提问,大家都热情参与到IDF论坛学术讲座中。

姜宇辉教授与观众Q&A集锦 :
Q:“当今各种媒介融合与强调观众参与感,不断突破电影的单向交流,是否意味着电影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消亡?”
A:第一,今天的电影跟以往的电影是不一样的,以往的电影在影院里或在家庭影院观看,是连续的过程,从头看到尾。从这个角度来说,遥控器发明的时候,是电影的死亡,因为你可以改变电影的线性运动,可以随便播放或暂停。当今电影变成网络方式传播,互动性极强。有一批学者认为游戏取代电影,就像电影取代之前的绘画、戏剧,这不是说以前的媒介形式死掉,而是综合的形式把各种各样的媒介形式包含在一起,这种观点认为电影要进化成游戏阶段。
第二,还有另外有一批学者认为电影必须抗拒这样的命运,真正的电影应该是有线性的叙事,这样观众才可以经历生命的历程,在里面有反思。导演给你启示,你通过这个故事想想世界,想人生,这里有很多艺术手法贯穿在一起。如果这个电影交在你手里可以随意摆弄,可以暂停倒放,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不是电影,这就是电影的死亡。
正反的两个观点,一个认为电影的游戏化,游戏的电影化,是电影发展下一个阶段;还有一个观点认为电影必须抗拒这样的命运,必须守住自己的底限——线性的叙事。我自己是倾向电影的游戏化这一方观点的。
Q:从这个意义上继续深入,有另外一个追问,今天的电影可以在家里看,电影院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A:今天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形态和方式,也跟以前不一样。观众看屏幕上的影像时,同时也会刷手机,也不是认真在看,电影被周围数码技术生活渗透。以前看《天堂电影院》,那个小孩叫多多,他走进电影院是神圣的感觉,会觉得那是天堂。今天有几个人走进电影院有这种感觉?现在的人们没有对电影的迷恋,坐在电影院里达到巅峰的体验已经没有了。
Q:电影从欧洲诞生到现在作为文化属性在不断消解?
A:迷影文化已经消解了,因为桑塔格提出对迷影的哀悼,实际上那篇文章就叫做《电影百年回眸》,就是过了100年之后再看一下,发现今天就没有人再迷了,也不可能迷,这是一个问题。
Q:您怎么评价《帝国大厦》这部电影?
A:我们今天研究帝国大厦是放到静止电影类。有两种考虑,第一(观点)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手法,以前电影一定要连续运动,有高速运动,有剪辑。但还有一些人认为静止电影实际上关注的不是“物”,是关注人的意识状态。《帝国大厦》不是让你看清楚这个帝国大厦有多高,他想让你转化自己的意识状态。通过一个对象,通过像的运动达到一种顿悟,达到意识流的阶段,指的是心,不是物,当然这个可能有人会从“物”的角度分析,但我看过《帝国大厦》这部影片,我个人觉得其实“物”的成分不是很突出。

Q:(这部电影)有OOO(以物为导向的存在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简称 OOO)的导向吗?
A:那时候没有OOO,哪怕这个景象是不动的,但仍然感受到观看者的在场很强烈。
Q:这个创作跟之前的创作很不一样,这是完全抹除掉人处理的方式?
A:对,但是可不可以说跟他的波幅也是有一些相似,比如波幅处理的是什么,原型与复制之间的关系。在机械复制时代没有原型,复制可以“杀死”原型,就是所有的复制品不断延伸。那导演拍摄《帝国大厦》时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你认为帝国大厦只有一个吗?他每一秒都在那里,那个镜头一直在那里对着他,一和多,原型与影像流动之间时间和空间静止跟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Q:纪录片作为一种媒介,跟人的关系是什么?
A:今天纪录片跟人的关系都有。《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纪录片属于 “框架“,会告诉你中国的食物是这样。第二种“能量”,就是流动,不是人在拍,是物传过来的。电影并不仅仅是影像,是传递世界的能量。第三种OOO,现在没有找到很好的OOO的例子,我觉得真的像Bozak一样, OOO是不是对电影本体的消解?你不要再拍电影,不要按照电影的方式拍电影可能就是OOO。
主持人:可能在纪录片领域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A:艺术家能做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是做一些评论。新的东西是不可预测的,所以还是期待纪录片导演未来会有一些自己的不一样的创造。
Q:“物”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从人的视角出发,是区别我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既然从人的视角出发,我觉得我们是无法评价,无法揭示的状态。离开人所有的感知,那“物”又是什么?物自己本身的形态是什么?怎样用影像来去表现“物”自己?我感觉这是悖论?
A:对,很多人都会提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当时我想到两个,第一个是媒介的第二种方式。你刚才说的人和物的关系是框架里面,人和物的关系是中介化,通过各种各样媒介也好、感知也好,通过这个物,通过当中的屏幕,我们跟物连接在一起,用这种方式来说,永远跳脱不出中间的屏幕,你有各种各样的框架,你不用镜头可以看到“物”吗,但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逆转?第一种方式是从框架到能量,你不是隔着屏幕,你确实感觉到外面不知道是什么,但有power,“物”有力量,“物”不是静止,等着你征服他。感知的背后是power,我写过这篇文章,但我认为这不是好路,但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是一种概念,叫做可逆性,强调人跟世界之间是可逆,我在触摸“物”的时候“物”也在触摸我,这两个是同时的,是互逆的,这就是一个逆转。我觉得你先在“人”跟“物”的关系中逆转出来。触摸如果是一个交互可以转化就说明物本身可以独立存在,原来是人摸物但也可以物摸你。这是另外一种。
其他我不是很赞同。我认为今天回到“物”的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体验问题。我今天不是从这条线上去想。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留给OOO,我觉得这两种方式是最好的,很难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今天我们看OOO好久没有人谈了,它就是一条死路。
主持人:可能你特别丰沛,所以特别容易投射。
A:我是以我观物,所以我只能回到更强烈的像体验,伤痛,我是觉得我可能太投射了。
Q:根据物质主义理论,刚才提到物质有能动性,你触摸它,它会有反映,这个意义上物质有能动,这个意义上“人”是否也变成“物”的一种,所以物物的可能性?
A:是的,后来有一本书《万物的民主》,作为生命的形态我们都是万物的一种我们是平等的。
Q:物质主义强调人和其他物是平等的,我们都是物,我觉得OOO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不是完全无人的状态,因为人本身也是一种物?
A:但你怎么达到这个平等,原来人文主义的东西需要去掉,情感、文化、欲望等等要淡化,所以它是个阶段,无我是个阶段,最后达到物的均齐,我是否跟之前“以我观物”是同样的,可能是不一样,意识的形态和面对世界的态度立场都发生了转化,可能是一种新我,不一样。
Q:我不一定非常赞同“生态电影”更多存在于纪录片里,它在故事片、剧情片也是存在。刚才您谈到Riverglass,讨论这部电影,他可能更多是从形式角度讲,生态电影的一个观点。是不是所有电影可以从生态电影角度解读,生态电影不是类型而是一种角度?
A:您这个观点我很认同。
主持人:但实际上长镜头是最花钱的,工业的消耗上最大,所以这很悖论。
A:但它给你的意识状态造成是最接近“物”的状态,这是“物”的结构,没有什么其他的。

主持人:我最后向姜老师做一个提问,您最后讲到生态电影当中沉浸式的体验,会让我联想到德勒兹在他的《时间-影像》当中提到,影像总是从某种混沌、停滞的居间当中重新找到一种力量,您觉得这两个东西有差异吗?
A:在德勒兹那里沉浸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他讲的是影像本体论,没有讲人的主观意识状态,这是他最大的问题。他应该讲影像怎么跟我们的脑子连在一起,德罗兹后面只讲到一点点,所以沉浸我觉得不是很重要。但你刚才讲的间断很重要,我觉得间断首先是“物”的阶段。其次,这个间断还可以造成你的意识状态或者体验状态的一种阶段,它是融合在一起。然后最终阶段我觉得像“中阴”,是生死之间的间断。因为它是一个断裂。
主持人:这也是你这篇文章最终停留未来的一个。
A:我开篇讲的进化就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数字是连续的,是我们人类意识下一个阶段;还有一种认为数字是深渊,是隔开我们人类的今天和明天,是断下去的。那我(的观点)是更接近第二种,所以不能叫做中间,我觉得应该叫做深渊,人类如果跨不过去,这就死亡了,我觉得它有一种临终关怀的意味。
最后,学术主持人周佳鹂副教授总结到: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让我们用哲学连接彼此的灵魂。哲学的意义就是带给我们思想某种程度的激荡,让我们在有困惑或不解时,意识到有很多人有和我们一样的困惑,但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已经给出了回应。这一点在后真相时代,在2020年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情景当中,对每个人都尤为珍贵。

学术主持人周佳鹂副教授

 浙公网安备 33010202002558号
浙公网安备 33010202002558号